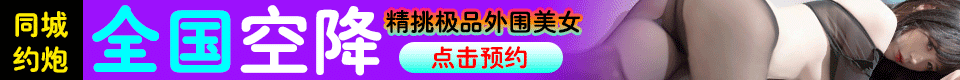拷问CIA 探员肯恩。理查森1-3
拷问cia探员肯恩。理查森
(第一章)
凌晨5:30,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沉睡中惊醒。
“理查森探员?”一个严厉的声音在话筒中响起。
“是的……”我含含糊糊地回答着,真希望能尽早结束这次意外的谈话。
“到0-700霍华德空军基地报道,你有新的任务在洪都拉斯。”严厉的声音
毫不含糊地下达着命令。
“是,知道!”我回答道,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这是一个什幺任务,它已经被讨论了好几个月。我曾经看过一眼报告,
其中一个任务是去搜集过去几年中在洪都拉斯最臭名昭着的贩毒头子——虐待狂‘处罚者’拉皮斯的情报。他在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他的古柯碱生意的经营范围扩大到了原来的几十倍,‘处罚者’正在失去任何的束缚和控制。我的任务是侦测并搜集到他扩充毒品生意的任何信息和证据——取得这些证据后就会申报到cia秘密部队那里,让他们去结束这一切。
我很快赶到了基地,见到了我的主管,资深长官迈克尔。穆斯肯基,一个四十三岁的男人中的典范,他另人羡慕的不仅仅是他那六英尺三英寸(185cm)的
肌肉身躯,更因为身为一名cia高级主管所具有的过人胆识和锐利的思维。他很快就在即将进行的洪都拉斯行动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我。
显然‘处罚者’拉皮斯正在秘密地绑架抓捕一些男人,强迫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与政府对抗,或是直接送到自己的古柯园里,他在洪都拉斯能很容易绑架到他们,或是在黑市上购买也不是问题。拉皮斯对20至40岁的白种男人很感兴趣,这就意味着(迈克尔。穆斯肯基的解释)他已经开始购买来自美国的男人……到现在为止已经大约30人了。所以要搜集到新的证据,在‘处罚者’自己无法停止之前,我们将让这一切都结束。
穆斯肯基告诉我前往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的飞机将在几小时之后起飞,到达后一辆货车将在机场跑道不远的地方等我,将带我要去接近拉皮斯位于帕图萨河沿岸的大本营。
领取了任务之后我被带到了衣帽间,用救生器材、长筒靴、通讯设备和一些现钞添满了我的帆布袋,橄榄绿的迷彩服换下了我的普通西装,里面穿着墨绿色的内裤,不穿袜子直接蹬上了长靴。我知道必须一切准备充分,光是都拉斯的酷热天气就是对意志的极端考验。
经过了六个小时的飞行,在墨西哥做了短暂的停留,换乘了另一架航班,飞机在特古西加尔巴着陆了。果真象穆斯肯基所说的,一辆白色丰田货车正孤零零地在飞机跑道不远处等着我。
晚安……“年轻的司机对我说。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南美洲人,身上散发着积攒了一整天的汗味。”我听说你要去监视拉皮斯?“
我向他微笑了一下,把大包放到了车后座上,说道:“是的,似乎‘处罚者’需要有人照看他一下,不过我想那时你会远远地离开我吧?”
“当然了……”南美栳急忙回答道,“我们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最后两小时将会很颠簸。我只能拉你到距离拉皮斯的城堡一里远的地方,然后你得攀登到一个悬崖的顶上,那里就能俯瞰到他全部的古柯种植园,那里你能很好地得到你想要的。”
“好,听起来不错。”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双手枕在脑后,把身体调整到比较舒服的状态。
晚上11:30左右,我的屁股经过了上窜下落的剧烈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
南美佬把车停了下来。
“好了,我们到了,你的路在那。”他的手一直指向被棕榈树掩映着的一个山岗,“顺着这条路,用你的指南针朝着东北方向步行,爬到头就是那个断崖顶了。”
“哦,这就到了,”我把车后座上的布袋背在身后,“谢谢,,我知道你回去还有很长的路,所以小心点。”
“一定……”他挤了一下右眼回答道,“你也小心,我知道拉皮斯抓住过以前的特工,但我听说你是最棒的之一,我不想失去你。”
“我也不希望被拉皮斯抓到,”我坚决地说道,“拉皮斯是我的。”
在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下,小货车开走了。我拨开层层繁密的枝叶开始了徒步前行。蚊子很多,我马上从背袋里拿出了杀虫剂有效地阻止了它们的进攻。
早上4:30,我结束了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到达了断崖的顶端。曾经在照片
上见过的古柯园真实地映进我这个目击证人的眼帘。我摘下背袋,从断崖悄悄地爬了下来,潜伏在这片巨大的古柯园边缘的一些建筑的后面,仔细地观察着。很多巨大的火把照亮了园子,使得即使在晚上也能进行收割。即使渐渐在天际闪现出的红色的朝阳极其刺眼,但使用我的夜视摄像仪却能够很清晰地看清一切。我惊讶于夜视仪中传过来的画面,我看见很多的穿着衬衫的男人在采摘着古柯叶,四座高耸的警戒塔,还有很多牵着狗的警卫逡巡在园子周围。我的夜视仪能够照相并emill回总部,我需要选择一些重要的镜头,于是试图给那些正在采摘古柯
叶的男人们一些特写。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健壮的男人,年龄不等,穿着磨损破旧的牛仔裤,光着脚,每个人都相互间隔着10到15英尺远的距离。
趴了一个小时,汗水早已糊满了我的身体,我蹲下身,脱掉了黏糊糊的迷彩服。我结实的胸肌在早上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回到了放背袋的地方,拿出水壶补充了一下水分,简单嚼了点干粮补充了一下体力。我必须要再靠近一些,以便捕捉到更多的信息,于是我我潜伏了二十码左右躲藏在一个岩层下。可是这是我致命的错误,由于岩石的背面没有树丛,所以我马上就暴露给了守在外端的守卫们,直到最后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幺大的一个错误。
我听见身后传来的叱骂,我的身体一下就僵住了。卡拉仕尼科夫冲锋枪的枪筒硬邦邦地戳在我的屁股上。
“一动也别动……美国杂种。”一个生硬的英语传了过来。
另一个声音说道:“慢慢举起你的双手,别出一点声,你就会发现你会活着。”
我的心仿佛要蹦了出来,所有的念头闪现在脑海中,随即就都消失掉了。我放下了夜视仪,把双手慢慢举过了头顶。一双手抢过了夜视仪并把我的双手牢牢地铐上了。这时枪筒从我的屁股上挪开,我慌张地转过身,我摇晃着脑袋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面前的三个守卫,紧张地说不出话来。这时其中的一个守卫举着对讲机用西班牙语在报告着我被捕获的事情,那边回复让他们把我立刻带到城堡里去。一个守卫在他们带来的袋子里拿出了个连着细绳的粗布袋,他把它套在了我的脑袋上,并把细绳在我的脖子上扎紧。脑袋套着袋子的我,仿佛掉进了无尽的深渊之中。我被推搡着踉踉跄跄地走在坎坷的土路上,有几次差点摔倒在地上。
最后终于到达了这个古柯种植园中最大的一个建筑物前。
我们进了这个庞大的建筑物,两个守卫紧紧控制着我的双肩。这时一个守卫用西班牙语大声地呼喊,我猜想他们可能在告戒其他的守卫他们也许已经在美国反麻醉局的围攻之下了。几分钟后我(仍被罩着头套)被带进了一个房间,门在我的身后猛地关上了。我的身体被拧转了过来,一个硬邦邦的握紧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撞在我的胸膛上,随即又是几下重击旋风般地袭来。两旁的守卫继续牢牢控制着我的双肩,使我根本无法躲藏,这时又是一下重击火车般地落在我的后背上。
我喊叫了一声身体一下就弯了下去,可是控制着我身体的守卫却踢打着我的双腿,连拉带拽地让我又直立起身体,去继续承受那一下又一下的猛烈击打。当又一拳头击在我的右肋时,我疼得几乎要窒息了,收紧的心脏仿佛缩成了一团。这时击打暂时停顿了一小会儿,可是没有任何的提示,惩罚的拳头又沉重地击打在我的阴茎和阴囊上,我感觉阴囊仿佛要在鼠溪处爆裂开了,不得不痛苦地喊叫起来,但迎面尔来的拳头仍是毫不仁慈地击打在我的鸡巴和卵蛋上。我痛苦地请求他们停下来,也许他们知道我已经被打得够戗了,终于把我扔到了地板上。我反铐着手,象个婴儿似的蜷缩着身子,并不断地在地板上来回滚动伸缩着身体,试图减轻一下我那几乎被打爆了的鸡巴和阴囊上的剧烈疼痛。
门开了,又进来了几个人。一个操着生硬英语的人下了命令:“把他的头套和手铐都解下来,把他弄到椅子上去。”
我的身体被拉了起来,手铐也从我的手腕上解了下去。当头套从我的脑袋上被拉下后,我习惯性地眯着眼睛打量着这个被灯照得很亮的没有窗户的房间。我被推搡着坐在一个破旧的木椅上。现在我可以很清楚地看清面前的这些人,他们都很健壮,黝黑的肤色,除了那个说英语的外都是胡子拉碴的。那个人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穿着洪都拉斯人常见的牛仔裤和皮靴,结实硕大的胸肌上挺立着两个黝黑的乳头。他双手背在屁股上,正仔细地打量着我的身体。他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我的面前,脸上挂着严厉凶狠的表情。在他的右后侧站着的守卫就是刚才狠狠教训了我的人。他伸出双手,抓在我的迷彩服上,几下就把它撕裂了,并完全扯了下来,我健壮的胸膛一下就暴露了出来。我光着上身坐在那里,大张着嘴,瞪着惊恐的眼睛,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吃惊不已。
讯问者把脸靠的更近了,双手按在我的椅子的扶手上。他弯下腰,脸距离我的脸只有一寸左右,凶恶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你叫什幺,美国佬?”
我把脸转到了另一面,我几乎能闻到他的呼吸,真是另人厌恶。
他拧着我的下颚把我的脸转向他,又重复地问了一遍。
“我的名字叫肯恩。理查森。”
“年龄?”他高声喊道。
“36.”
“你是个美国军人吧?”他愤怒地吼道。
我没有回答,把目光移向别处。他的右手狠狠扇在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然后又抓着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拧向他。
“你还有别的部队吗?”他高声咆哮着。
“没有。”我回答。
“cia(中情局)?”他问道。
我再次沉默。我不能给他更多的信息。我知道他不是‘处罚者’拉皮斯。他握紧了拳头狠击在我的胃部,震得我的脖子和下巴上的汗水溅落早我的胸膛上。
然后他又几个重拳打在我的小腹上,剧烈的疼痛让我咳出了眼泪。
“你个美国杂种!”他怒骂着,最后的击打在我那已经受伤的鸡巴和睾丸上登陆了,由于剧痛我的身体弯成弓形,尖声的嚎叫象针一样尖细。讯问者转向其他的守卫,用西班牙语告诉他们把我弄到拷问室,然后咆哮着冲出了门,两个守卫跟随着他也一起离开了。
剩余的三个守卫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两个守卫紧紧抓着我的手臂,他们把我架出了房间,走进了黑暗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他们打开了一扇巨大的铁门。我的挣扎毫无意义,他们拉扯着我顺着长长的楼梯下到了地下室。随即另一扇铁门被打开了,我有被拉进了一个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中间,我们在另一扇门前停了下来。一个人打开了门,我被拽了进去。
我转着脑袋想从他们的脸上发现任何一点仁慈的迹象,但我失望了。
这是一间拷问室,一张巨大的木拷问台立在屋子的中央,天花板上挂着明亮的灯泡。墙边是一排安着玻璃门的巨大的白色壁柜,透过玻璃很容易就看到了在那些小橱格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用来拷问男人的器械。我惊恐地看见了电极、宽厚的皮带、连着电线的肛门塞还有众多的各式各样的夹子和螺丝钳,也许是用在乳头或是身体的其它部位上的。这里简直就象一个邪恶的sm医生的工具间。那里还有许多装着药丸的瓶子,皮管,细长的橡胶管——就象那种插入阴茎用来导尿的导管。在房间的后面我还看见了两个看上去十分可怖的机器,其中一个机器的上面竖立着一根粗大的阳具,上面还缠绕着一根长长的橡胶管;另一个机器很明显是用来上电刑的。机器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第二章)
他一边用西班牙语吩咐守卫把我的衣服全部扒光,一边从一个壁橱的格子里拿出了几个药瓶。两个守卫继续控制着我的双臂,另一个守卫转到了我的正面。
他解开了我的迷彩裤并把他褪到了我的膝盖下面,露出了我那已被汗水湿透的墨绿色的军内裤。
“不,上帝,请不要……”我请求着,“请让我见拉皮斯,我想和他面谈,请求你们,你讲英语吗?”我不断向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请求着,可是他对我完全视而不见。我急切地希望他能对于我的请求做出反应,甚至没有注意到一个守卫已经抬起我的一个膝盖以便脱去我的靴子。很快两只靴子就脱离了我那湿漉漉的大脚,随后守卫们就把我的裤子完全扯落下来。当我几乎完全赤裸地站在那里后,两个守卫又一边一个牢牢控制着我的双臂使我丝毫也动弹不得。这时那个医生走到我的面前,开始查看着我那健壮的肌肉躯体。我胸膛上的肌肉疙瘩甚至由于极度地恐惧而不停地抖动。
“我很喜欢你这个家伙……”他用轻柔的嗓音认真地对我说道,“通过这些淤痕,我猜到他们已经对你简单地‘招待’过了。”他直视着我的脸:“我要好好地整整你,所以你最好别招供的那幺快。事实上,当我对于男人的尖叫声感到厌烦的时候就回把他们的嘴塞上。你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身体,这就意味着我很有兴趣长时间地拷问你。顺便介绍一下,我是弗兰肯大夫,你叫什幺?”
“你个杂种,虐待狂杂种。”在极度震惊之中我对他咒骂着:“你个不得好死的野杂种!”
弗兰肯看者我,轻微地摇了摇脑袋。“我从没遇见过你这种类型的。很多送到我这里来的男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洪都拉斯人,都恐惧得要命,都是低卑地向我乞求仁慈和宽恕,跟我讲他们的孩子或是所爱的人。当我得到一些真正的男人,比如你,意味着在你身上还需要做的更狠一点。”他绕到我的身后,一边检查着我背后的肌肉,一边盘算着应该在我的身体上做些什幺‘项目’。当他转到我面前时向我展示着手里的两个药丸,一个大的粉红色的,一个小的是蓝色的。
“守卫,当我给他灌药的时候要好好按住他。”
“操,别想!”我试图反抗,但是守卫死死地控制着我,一个重拳击在我的肾部让我一下就瘫软了下来。大夫狠狠捏着我的下颚想迫使我张开嘴。另一个守卫扳着我的脑袋并死死捏紧了我的鼻孔。由于窒息我不得不张开嘴呼吸,大夫马上把药丸塞进了我的嘴并捅下了咽喉,‘亚当的毒苹果’经过我的咽喉时我被噎得要窒息了。“你个杂种,你在给我吃什幺?”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让我怀疑它仿佛要爆炸了似的。
弗兰肯抓着我的内裤两侧,把它褪到了我的脚下。我那软软的大鸡巴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中,并由于这意外的举动微微地弹动了几下,又圆又大的两个蛋正依偎在卷曲的黑色阴毛丛中。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红色的药丸很快就会让你的鸡巴硬邦邦地‘站起来’,
那个蓝色的会让你的意识迷失,让我很容易去审问你。”
片刻间药丸就在我的胃里融化了,并渗透进了我的血液。我摇晃着脑袋试图清醒,但眼皮却越来越重。“你个疯狂的狗杂种。”我沉重地喘息着。
“把他绑到桌子上。”弗兰肯命令道。
一个守卫抬着我的腋窝,另两个守卫拎着我的双脚把我放到了刑台上。我的挣扎在他们的控制下简直毫无意义。我的身体被极力地伸展,四肢大张,手腕和脚踝被厚皮带牢牢地扣在桌面上,另一条皮带横过我的胸肌下面。他们又拉过了另一条皮带,横过我的肚脐下面,把我的腰也固定住了。同样我的两个膝盖也被皮带绑紧,使得双腿没有丝毫的活动余地。在我平展的双腿之间,我惊骇地发现我的鸡巴已经高高地挺立了起来,并硬得象岩石一样。鸡巴上血管迸现,里面的血液被大力地挤压到了怒胀的龟头上。由于血液源源不断地在茎身血管里剧烈奔涌,使得我的鸡巴长到了足足七英寸多,甚至还在勃动着不停膨胀。弗兰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我,惊异在在我那立起来的大家伙上凝视着,粗长的阴茎醒目地挺立在阴毛和两个大蛋之上。当确信被固定在刑台上的我已经不会带来丝毫的危险后,大夫让两名守卫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名,毫无表情地握着他的卡拉仕尼科夫冲锋枪守立在门口。
弗兰肯大夫把一个装着满满工具和器械的小车推到了刑台旁边。我看着手推车,眼前一阵眩晕。艰难地呼吸开始告诉我药丸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从车上拿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球形口塞堵进了我的嘴里,唾液很快就淹满了球塞,恶心的味道似乎曾经在精液和尿液里面浸泡过,让我几乎要呕吐。当堵好了口塞,他从小车里又取出了一管润滑油,在他的两根中间手指上挤了很大一团,然后伸到了我的阴囊下面开始强行地往我的屁眼里插。在我的洞里他又厚厚地涂了很多的润滑油。
由于惊恐我那结实的胸肌不停地上下起伏着,试图与皮带做着无谓的抗争。当他的手指在向更远的深出探进时我不由得呻吟起来。
“非常好。”他说道,看得出他十分喜欢做这些事。弗兰肯从小推车上取出了一个很大的金属肛门电刺,这是一个末端带有一个圆球的又粗又长的金属装置。
他一只手扒开了我的屁股缝,把那个电刺深深地插进我的肛门,足足不少于八英寸,当最后的部分也全部大力地捅了进去,我疼的后背都要拱起来了。这时我的鸡巴去开始一下下勃动起来,他也注意到了这点,仔细地看着那里。然后转向了我的脸,挑了一下眉毛。
“你是个同性恋。”他微笑着小声说道。“你鸡巴上的反应出卖了你。”然后他吃吃地笑了起来。“当我在普通男人的身上做这些的时候,要他们的鸡巴竟相保持挺立,需要在药丸中加入四倍的剂量。而对于你,我的朋友,看来不用,我保证你将耗尽全部的意志去对抗极度的痛苦。”
我大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他,无法描述内心的悲伤和恐惧。他说的对,我是个gay.而且我深知我的这个隐秘一被揭穿,不难猜想,他们将会集中所有的痛苦在这方面击溃我。
“别用那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美国佬。我至少拷问过不少与四十个象你这样的家伙,他们都在为美国军队或是cia卖命。但是间谍先生,你对于我来说太棒了,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折磨一根漂亮的大鸡巴。”
我更加惊骇地看着他,汗水已经在我的胸膛和额头渗出,头发也已经被汗水湿透。
“我应该有个描述……关于你热腾腾的身体。没有多少人对于男人的身体能有这幺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我猜你大约三十多岁,不过,在三十多岁的男人当中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身体。我想,我现在应该去享受这个身体了。”
弗兰肯取出了三个金属鸟环,上面都安装着可以伸缩的螺丝装置。他把一个鸟环滑套到我阴茎的根部,被浓密的阴毛遮蔽住了。随着蝶形螺丝的逐渐拧紧,阴茎上的青筋和血管更加迸凸,当螺丝完全拧到头时,还夹掉了一些阴毛。第二个鸟环放置到了茎身的中央部位,当上面的螺丝被旋紧后,我的鸡巴开始胀成了红色。我注意到他正在看我的鸡巴,从尿道口的缝隙中正流出了一滴晶莹的腺液。
我的头开始有些发晕,药丸开始真真切切地让我感到痛苦。最后一个鸟环紧紧扣在龟头的下面,它被拧的如此之紧,使我的龟头被勒得剧烈地膨胀到疼痛难忍的个头。
然后弗兰肯从他的小车中拿出了二十个连着电线的金属夹钳,我的乳头先被钳住,引起了一阵尖锐的刺痛。我几乎无法尖叫,口水顺着口塞两侧的缝隙在嘴角流淌了下来。他又在我胸肌的上上下下夹住了几个夹钳,我的肚脐,毛发丛生的腋窝,双股内侧,四个脚趾,我的鸡巴和两个睾丸上也各自夹上了一个夹钳,还有两个夹在了静静躺在阴囊下面插在我肛门内的那个巨大金属牛刺上。他现在能看见我由于疼痛来回扭动着脑袋,两行泪滴正默默地流出了我的眼角。
他走到我的面前,用手在我的摸着我的脑袋,一个残暴成性的虐待狂现在却在安慰我:“我亲爱的美国猛男……你怎幺流泪了?我甚至还没让电机上的指针转动呢。我猜想你和你的那些古怪的同性密友们一定乐意享受这个,可是现在,你为什幺害怕呢?”
恐惧中我的脑海在飞快的旋转着,似乎记得在遥远的从前曾经一个皮革男人在我的鸡巴上使用紫罗兰棒时的快乐情形。
弗兰肯随即又回到了他正在着手的工作之中。他拿出了又一个插入物,那是一个又长又细的柔软的塑胶管状的东西,在它的底端同样连着电线。他又拿出了装有润滑液的瓶子,把塑胶管插到了润滑液中,然后把沾裹着亮晶晶润滑油的塑胶细管抽了出来。
即使我的大脑处在眩晕之中,但我也知道他要做什幺。他要把这个连着电线的细管插进我的尿道。我极力地想活动身体以来抵抗,但随着皮肤的挣动,狠狠夹在身体上的尖钳似乎要咬裂我的皮肤,使我不得不停止这没有意义的反抗。
残暴的大夫牢牢地抓着我坚硬的鸡巴头,另一只手把那长管插进了我的尿道。
当裹着润滑油的细管在我的尿道里缓慢而又坚定地深入,我真切地感受到到里面传来的疼痛。细管穿过了笔直的茎身,最后戳到了前列腺上。
“就是这里。当管子捅到头的时候就会弯曲了,我确信当一切开始的时候你将真实感觉到他的存在。我还有最后一项事情,你那充满精液的巨大睾丸需要再拉长一些。”弗兰肯从车上又拿出了一个黑色皮革‘降落伞’(用来拉伸阴囊的伞状器具),把它紧紧拴在了我多毛的阴囊根部。当拴好后他又用力拉了拉以确认巨大的卵袋已被牢牢地卡在伞槽上。他在‘降落伞’上接上了一个铁链,铁链至少三英尺长,穿过我的两腿之间伸延到刑台外面,挂在了一个齿轮上。弗兰肯那只邪恶的手开始摇动那个齿轮,使得我那松弛的链条慢慢地拉紧。我的身体开始禁不住地颤抖,当链条全部被拉直后,齿轮还在继续转动,我那硕大的阴囊也开始感觉到被拉扯起来。包裹在阴囊里的睾丸又被唤醒了一小时前被痛殴时的疼痛。并且随着延伸器毫不留情地撕扯着阴囊,一开始还很迟钝的痛感变得越发尖锐起来。当阴囊被远远拉离了我的身体后,我那一直向上挺立的坚硬鸡巴也慢慢地拉斜向45度角。当紧拉着阴囊的齿轮做了最后一次旋转,我感觉里面的两个睾丸几乎要被拧碎了。然后链条就被牢牢地固定在那里。这时在深插在尿道里的细管周围已经开始渗出腺液,并聚集在箍在龟头上的第一个鸟环的上面。
由于看到了我流出的腺液,弗兰肯嘻嘻笑着,“美国佬,你应该知道,你的精液是为一个卓越的电刑拷问者流的。”他用手抓在我敏感的龟头上,把上面的精液涂抹到我直立的阴茎上,此时我所做的只有痛苦地呻吟了。夹钳在刺痛着我的皮肤,肛塞在惩罚着我的肛门,鸟环在折磨着我作为男人的标志,‘降落伞’在狠狠延展着我的大蛋。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深插在鸡巴里的尿道管,我从未有过任何器物插进尿道的经历,这种独一无二的痛苦真是我无法忍受的。汗水、泪滴、唾液和颤抖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体上上演着。
第三章
拷问师这时把连在夹钳、肛刺、鸟环上的电线接到了电刑机上,然后拉过了一把椅子坐在拷问台旁边的电刑机前。他戴上了一幅眼镜,以至于能清晰地看清并准确地控制电刑机上的刻度盘。他按下了这个看上去应该是50年代专门为电刑拷问而制造的橄榄绿色的机器上的开关,随着机器开始发出嗡嗡的声响,四个仪錶盘上的指标仿佛有了生命。没有任何的提示,他就拧动第一个仪盘,仪盘上的显示着从一到十。我立即感觉到来自我那勃挺的鸡巴上的麻刺痛感,而且这种刺痛还在逐渐加强。
这时他突然开始操作另一个仪盘,从肛刺传来的强烈电流猛地就击穿了我的肛门和前列腺,我抽搐的直肠一下就紧紧包裹住了肛刺,而且屁股也控制不住地从拷问台上拱了起来。我的阴茎持续着麻刺的痛感,而这种钝胀的疼痛使得我的阴茎挺得更加坚硬。然后弗兰肯又拧开了连接着5
个夹钳的仪盘上的旋钮,这时恐怖的电流冲击波贯穿了我的全身。仅仅15秒
左右,我就闻到了我的胸毛和阴毛燃烧的气味。
然后他停止了在鸡巴上的电击,却把连着肛刺的仪盘从刻度4旋到了刻度7,
我的直肠连同着肛门马上就进入了痉挛的状态。事实上,连接着肛刺的夹钳紧贴着我包裹着睾丸的阴囊,以至于我的两个大蛋也在承受着额外的电流冲击。我庆倖弗兰肯暂时还没有增加专案的打算,这时臭烘烘的黏液已经从我的屁眼中流了出来,混合着汗水慢慢地滴淌在拷问台上。黏液被电流加热而变得滚烫使我更加难受。这时我的肛门还在持续着电流的冲击,而且他又旋开了连着另外五个夹钳的按钮又一次让所有的指标都指到了刻度5的位置,足足20秒。我的身体开始抽搐翻腾,仿佛要挣脱开皮带的束缚。大量的口水涌出了我的嘴角,胸毛和阴毛烧焦的气味充满了整个的房间。
弗兰肯终于关掉了连着肛刺和夹钳的控制盘,恩赐给我几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大口喘息着,当空气流进了我的肺,我感觉胸腔仿佛在被重重地敲打般疼痛。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弗兰肯站起了身,示意那个站在门旁的守卫让来人进来。
守卫打开了门,进来了一个穿着衬衣被健壮胸肌顶得鼓鼓绷绷的男人,就是一开始在我身上练拳击的那个人。
“你好,伯纳德。”弗兰肯用西班牙语问候道着,然后他向伯纳德介绍说我是个gay,并且告诉他准备对我进行更多更严厉的拷问程式。
伯纳德笑了笑,用西班牙语告诉弗兰肯我的名字叫肯恩。理查森,36岁,是
个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他说他们已经检查过了我的背袋,在里面找到了不少东西,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事情,所以伯纳德十分赞同增加对我的拷打时间和拷打强度。弗兰肯愉快地答应了,并且用西班牙语告诉伯纳德他将会为我注射一种药剂,能防止我在疼痛中昏厥。当伯纳德向弗兰肯问他是否可以观看一会儿时,弗兰肯毫不忧郁就点了头。
“好了,肯恩探员,”
弗兰肯医生笑着说道:“你已经休息得很充分了。”说完,他就把连接着深插在我尿道里的细管的那个控制盘扭到了刻度6的位置上。我的鸡巴一下就变成了血红色,而且完全失去控制地猛烈痉挛弹动着。这疼痛是如此的强烈,我的眼球疯狂地滚动,甚至完全转到了后面。我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缩紧了,舌头也狠狠地抵在口塞球上。鸡巴上的猛烈拷问足足持续了至少20秒,弗兰肯才把控制盘上的指标拧到了2
的位置上。他瞅了瞅伯纳德,伯纳德一只脚别着另一只脚地站着,相互交叉的双手抱在胸前,正凝视着我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身体,视线固定在我那巨大的勃起物上。这时他把脸转向弗兰肯示意他继续,弗兰肯把连接夹钳的钮旋到4
,把连接肛刺的钮旋到了8.这时我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在一起承受着电流的打
击,它已经开始让我失去意识。
“快给他注射!”伯纳德连忙说道,“让他保持清醒!”
弗兰肯从椅子上跃了起来,走到墙前,从壁柜里拿出了一个注射器。这是一个很长的注射器,底部有一个圆形的钩,手指能够穿进去,使得在注射期间能够非常稳定。他把注射器上的长针探进了我的阴毛,贴近了我的直立着的阴茎。
“哇!!!!”弗兰肯尖叫着,迅速地撤回了针。“妈的,他电着我了!!!
电流击透了针尖。“他关掉了电刑机,我那上拱着的身体一下就落到了刑台上。
但我的鸡巴却依然在不停抽搐着。他完成了注射,我感到一股凉爽的液体顺着我的盆骨一直进入了我的身体,并很快就控制了我的身体,强迫我的意识变得清晰而敏锐起来。我眨着眼睛四周环视,看到了正在坐在电刑机前正在休息的拷问医生。然后我又看见了伯纳德,我摇晃着脑袋试图恳求他。他却向我笑了笑,然后把目光移到了我汗漉漉的躯体上。
重击!重击!重击!3次超级强烈的电流冲击着我的阴茎和尿道(它一定是
在刻度10上)。我的头‘嘭嘭’地撞击着木桌面做着回应。又一次……重击!重击!重击!又是4次强烈的电击在同样的位置上。紧接着,又是5次!这一连贯而又持续的在我鸡巴上的电击总体上都是在10级刻度。燃烧的阴毛此时已经在室内散发着臭味。紧接着,肛刺和夹钳上的电击开始了。同样也是10级,夹钳上的电流扎刺着我从上到下的的全部身体,从脚趾到已经几近烧焦的乳头。他把肛刺上的电击控制在5级,但却是不间断的持续电击。没有任何的提示,夹钳上的电流也开始从脉冲状态变成了持久式的电击,弗兰肯用手抓住了我的鸡巴,他小心不触碰到箍在上面的金属鸟环,而是一把抽出了插在其内的尿管。管子已经变成了黄色,而且上面还粘附着大面积的块块血斑。可是我的阴茎却依然保持着坚挺勃立的状态。他回到了电刑机旁,关闭了连着夹钳的按钮。却把连着肛刺的电钮拧到了刻度7的位置上,并且调成了脉冲式的电击去进攻我的肛门。接着鸟环上的电击也被调到了刻度7上,去配合肛门里的电击。他做到了,而且特意让两股脉冲式的电流不同步,交替着进攻我的身体。肛门中和鸡巴上的长久电击引诱我的身体产生了兴奋,这个该死的杂种要强迫我来一次射精。操他妈的,我心中咒骂着,这样下去肯定会在极度的疼痛中从我那被电流冲击着的前列腺中压榨出精液。果然脉冲的电流变得更强烈了,撞击着我的前列腺,而我的直肠也因为电流的加强更加有力地裹紧了肛刺。
伯纳德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知道弗兰肯要给我来一个痛苦中的射精。弗兰肯继续拧动了控制盘上的按钮到了刻度8的位置上,我的鸡巴开始更加猛烈地抽搐,为着一次随时都可能进行的射精做着准备。这时在我体内冲击着的电流仿佛从痛苦的拷问变成了一次凶猛的‘挤奶’行动。
我已经不能控制住我的身体,脑袋猛烈地来回扭动着。全身汗如雨下,飞溅的汗珠甚至迸到了伯纳德的身上。痛苦的哭喊声沖出了我的喉咙,声音是如此之响,仿佛堵在嘴里的口塞球已经不存在了似的。
控制盘最后被旋到了刻度9,电刑机开始嗡嗡地晃动起来,仿佛是因为如此
长久的工作而显得有些疲倦了。我的前列腺已经完全无法控制了,精液开始从我的鸡巴中有力地喷射出来,疼痛得感觉就仿佛细碎的玻璃渣子从我那如同燃烧的鸡巴中喷发出来了似的。一股,两股,三股,四股,五股粘稠的精液从我的鸡巴头上射出,仿佛炮弹似的落在拷问台的中部和远处,然后三股力量稍小的精液喷落在我的阴囊上,最后一些残余的精液从龟头上涌出顺着阴茎向下流淌着。残暴的医生和伯纳德惊异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击垮了我。脉冲的电流继续冲击着我这经历了剧痛中的高潮后的身体。弗兰肯终于关掉了机器,我那耗尽体力疲惫不堪的身体重重地落到了拷问台上。
“太棒了,弗兰肯!”伯纳德用英语高声喊叫着。“我认为你已经让他一辈子也忘不掉了。而且。刚才你说他是个gay?”
弗兰肯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时他漫不经心地从我的肛门中狠狠拔出了肛刺。
“噢,真他妈噁心!”看到肛刺上沾满了黏液、润滑油和粪便,伯纳德用英语大声叫道。
“你愿意舔一舔吗?”弗兰肯用英语笑着打着趣。
伯纳德捂着鼻子摇着脑袋离开了房间。
弗兰肯开始摘除我身上的夹钳,当夹钳离开了我的身体,可以清晰地看见留在我胸膛、乳头和双股内侧的烧灼伤痕。电击鸟环也被脱下了,精液味混合着浓重的阴毛烧焦的气味简直让人窒息。他耐心地清理着我那依旧挺立着的阴茎,它已经被精液糊满了。最后他松开了箍紧了我的睾丸并极度拉伸着阴囊的‘降落伞’,我那拉紧绷直的身体终于可以舒缓一下了。他取出了我的口塞,我的下颚因为被如此长久地撑开而剧痛不已。
“守卫,”弗兰肯召唤道,“帮我把理查森先生从上面解下来。”
那个始终守在门边的守卫放下了枪迅速离开了,很快就叫回了另外两个守卫,
一起把我从皮带中解了下来。一个守卫把我的腿拌到了台下,让我的脚支在地上。
我很快就瘫倒了下来,这次拷问是如此地严厉,我根本无法自己支撑住自己。
守卫急忙抓住了我的身体。我那根依然挺立的鸡巴随着我摇晃的身体而不停摆动着,把上面残余的精液滴落在地面上。
“妈的,这个家伙真他妈臭!”一个守卫一边扶持着我的身体一边用西班牙语骂道。
“把他关到9号牢房里,他会喜欢他那里的伙伴。拿着这个,他需要穿点东
西遮挡一下他的那根硬鸡巴,它至少还得硬上5个小时呢。”
弗兰肯一边吃吃地笑着,一边扔给守卫们一件窄小而又破旧的比基尼泳裤。
“一个同性恋男人应该喜欢穿着这个性感的白色小裤衩。”
然后我被赤裸裸地连拖带拽地弄进了走廊,我的鸡巴伴随着我踉踉跄跄的步伐而不停地上下摇动着。我们走到了走廊的尽头,进入了一扇上了锁的金属门内,然后沿着另一段楼梯下到了更深的地下空间。在这个走廊的两侧有很多的小间,每一侧都是十个。看上去一半是满的。我无法全部看清关在里面的那些囚犯,只有几个站在铁栏的旁边。似乎他们大部分都是白人,都只穿着破旧的内裤。被佔据着的每间牢房都关着两个人。我孤助无援,并且感到万分的困窘,因为他们都在看着这个被守卫带来的新人挺着根坚硬的大鸡巴,它无疑在告诉所有人我刚刚从那个地狱般的拷问室回来。我知道同他们一样,我这次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去那间拷问室,因为有人喜欢在男人的身上做这些事情,那个人就是‘处罚者’拉皮斯。我知道到达了关押自己的牢房,因为守卫们已经打开了门。我们进到了里面,他们把我扔在了一个小铁床上那臭烘烘的污秽不堪的床垫上,对面是另一个家伙。
他们把我的身体扭转过去,让我后背朝上地趴在床上,并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位置,然后把那个白色的小内裤扔到了我的后背上。
牢房门砰地一声关闭后,守卫们离开了。
第四章
在我对面的小床上坐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军人,看上去也刚刚遭受过残酷的折磨。他坐在那里注视着我这筋疲力尽的身体,我全身光溜溜的,散发出来的臭味很快就散满了狭小的牢房。那个军人下了他的床然后走到门前向外巡视了一下,然后走到了我的身边。他跪在了我的床边,把手放在我的床上。仔细地观察着正艰难呼吸着的我。这名军人惊异于那些南美佬究竟在我身上弄了些什幺,我的皮肤由于遍布其上的淋淋汗水而闪闪发亮。
过了片刻他把头更靠近了我对我轻声问道:“你怎幺样?”
残酷的拷问让我丧失了意识,已经做不出任何的反映。
“你能听到我吗?”他继续问道。看到我依然没有反应他把手指放到了我的鼻下确认我仍然在呼吸着。为了使我的姿势变得舒服一点,他抓着我的胳膊挪动着我的身体,然后把我的腿也并拢在一起。后来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我那被强烈电得红肿的肛门,甚至发现了我的阴囊也是又红又肿大了很多。他从我后背上拿下了那个小白内裤放到了我的脚边。然后军人回到了他的位置坐在自己的床上同情地看着我。
足足不少于三、四个小时,我只是偶尔在昏迷中翻动一下身体。这个军人一定很高兴他至少也有了个狱友,他想让我变得更舒服一些,于是想把我的身体翻过来。
“嗨,朋友,”他再次向我轻声地问道,看到我依旧没有反应,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抓着我的双肩试图翻转我的身体,让我的后背取代我被压在床上的胃部。他用尽全力挪动着我那195磅重的肌肉身体,使得我的身体微微前移,然后扮着我大腿的内侧,让我的后背翻转了过来。我的身体摇晃着跟着转了过来,这时我那随着身体翻转而摇晃着的坚硬的鸡巴一下就跳进了他的眼帘。我躺在那里,依然闭着眼睛,嘴微微张开着。
他被抓到这里后不止一次看到过勃起的阴茎,但还是惊讶于我的粗度,还有那硕大的龟头。他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的身体,看到了在我的鸡巴、大腿、乳头、和胸膛上的被电流烧灼过的伤痕。难怪这个人失去意识,他想到,他们居然给他夹了这幺多的电钳。
我开始眨起了眼睛,而且试图去吞咽吐沫去缓解我那干巴巴的嘴。
“嗨,嗨,男子汉!”军人说道,“你是好样的,现在感觉怎幺样?”他轻拍着我的脸颊。
这时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已经能看见了牢房内那灰蒙蒙的颜色,并努力眨着眼睛去适应室内的灯光。
看到我正在恢复知觉,军人赶紧把那个小内裤覆盖在我那坚硬的勃起物上,虽然这个努力微不足道,但却是唯一的。
“我的脑袋好象在被敲打。”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手放在太阳穴上用力揉搓着,“这场该死的折磨!”
“现在好了,他们不会再打扰你了。”军人平静地说道。
我看向他,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貌,精干的短发,不多的胸毛,结实的二头肌和宽厚的肩膀,粗壮的两条大腿。我能感受出他是真的在关心我,可是我低下头却尴尬地看见了被白色内裤遮盖着的挺立着的鸡巴。
“这个小内裤根本遮不住那里。”我闭上眼睛羞耻地说道。
“还不错,我转过头去,你就可以穿上它了。”
说完他站起身并转过了头,我看见他穿的也是一个类似的内裤,不过是深绿色的。
我抓起了内裤把它套到了腿上,并颠当着身体把它从腿上拉到了腰部。我的尺寸是32号,可这个小内裤最多也就28号,所以当我艰难地把内裤穿上后,我鸡巴的轮廓仿佛浮雕般地凸现在紧绷绷的裤衩上,并且我那挺立着的鸡巴上面三分之一的部分伸到了内裤的边带外。他转过了身,坐到了他的小床上。我也从床上爬了起来,和他面对面地坐在床上。
“你叫什幺名字?”我严肃地问他。
“杰德。”他回答到。
“你是怎幺到这来的?”我问到。
“我隶属与北卡罗莱那州第34军团,我和我的一个排被派到洪都拉斯完成一
个维持一个旅客通道不被地方匪徒骚扰的为期三个月的任务。可是一星期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在行军中遭到一群武装暴徒的袭击,把我抓到这来了。”
“那你的部队一定在四处寻找你。”
“是啊,我业这幺希望。汉克也被俘了,被关在另一侧的牢房里。他是我们的排长,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我们。”
“他们在你身上做什幺事了吗?”我深喘了口气问道。
“哦,是的。”杰德回答到,“他们把我抓到这时是黑夜,所以我根本无法弄清这是哪里。他们收缴了我的武器,脱掉了我的军服,只给我留了这条内裤。
然后把我推进了一个非常小的牢房,小得我只能蜷伏或是跪着。我在那一直待到早上,然后他们打开了牢门,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抓着我,把什幺东西放到我的鼻子下面。那一定是某种化学药剂,我的意识一下就模糊了。“
“这个穿白大褂的人把你带到了一个象是手术操作室的房间里了吗?”
“噢,是的,我猜你会那幺称呼它的。”杰德说道,“这个家伙脱掉了我的内裤,让守卫把我绑着手腕吊在那里。那时我完全光着身子,然后他在我的鸡巴上注射了一种什幺药剂。”
“他对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我敢打赌里面的药剂和你的不同。”
“无论是什幺,反正它让我全身的神经末梢都变得异常的敏感,而且,而且还使我的阴茎硬起来了。”
“是不是他们也电击你了?就象在我身上做的一样。”我问到。
“不,他们没有电击我。他把我吊在在一个奇怪的机器前,把我的硬鸡巴塞到了一个管子里面。操他妈的这个家伙,开始折磨我,那个该死的管子对我的鸡巴又是压榨又是吮吸,至少30分钟的时间。”
“这个机器是不是在强迫你射精?”我有些猜出来了。
杰德点了点头,“是的,我根本无法控制,于是就对那个机器里射了精。我看见我的精液顺着管子进入了那个机器。但是那个家伙并不仅仅想在我身上做一次,他让人解开了我,有把我用皮带固定在木台上,然后他离开了房间。我猜想大约45分钟后他回来了,又把我吊了起来。这个白痴又给我注射了一次,让我再次勃起了,然后又把我吊到那个机器前。这时我乞求他不要再做了,他根本不理睬我,仿佛我完全不存在一样,甚至始终他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次让我射精用了比较久的时间,他好象有些愤怒了,他把机器上的马达调到了最大状态,让那个该死的管子疯狂地压榨吮吸我的鸡巴。那个杂种又接连两次把我吊到了那个机器上。”
我坐在那里,心脏砰砰乱跳,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被吊到那个机器上。“然后他们就把你关到这里来了?”
他点了点头,目光低垂。“最后一次吊在那里我已经射不出任何东西,他焦躁地围我转着圈。当他发现我实在射不出精液了,他气哼哼地关上了机器,把我的鸡巴从管子里一下就抽了出来。由于如此长久和强烈的压榨和吮吸,我的鸡巴上竟已被擦伤了。然后他拿过来一个连着细绳的黑头套和这个内裤,他把这些都给我穿戴好了,绳子紧紧地系在我的脖子上。然后叫守卫把我关到这个牢房里了。”
“我的上帝!”我说道,我真担心那个杂种也会在我身上做这样的事情,“你说你已经关在这里一个星期了?”
“是的,大约一星期了。你刚来,真的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守卫们随时抓来一些人关到牢房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我不知道,他们给不给你们食物?”
“你能叫它们是事物可太好了。”杰德有些恼怒,“只是一些乳酪玉米饼,所幸的是水很充足。有时给牛奶,还给了我们一次胡萝卜。”
“哦……”我说道:“拉皮斯一定在从事贩卖奴隶的交易。”
“什幺?你这幺认为?”
“一定是这样。”我回答到,“这就是一个从事奴隶贩卖而修建的城堡。他们抓获俘虏,折磨他们,摧残他们,然后把他们卖到出高价的买主那,我打赌他准备要从古柯碱生意中脱离出来了。”
这时,从走廊尽头传来了铁门把打开的咣当声,随之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
当守卫们的脚步声靠近的时候,我和杰德都沉默了。他们打开了关着汉克的牢门。
“快出来,马上!”守卫喊到。我走到牢门的小窗前,向走廊看去。他们抓着汉克,并强行地给他戴上了手铐。他们推搡着汉克向走廊尽头走去,汉克一直咒骂着他们。
“你认为他们将要在他身上做什幺?”我问杰德。
“杰德下了他的小床走到了门前看着被推搡着远去的汉克,他摇了摇头,”
汉克是我们的排长,他是个好样的。他总是在反抗他们,他假装自己隐藏着什幺秘密的情报,其实他并没有。他们每天都会把他带走,每次回来,他的状况就象你刚才进来的那样。“
“他应该学会闭上他的嘴。”我说。
“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电击过他的鸡巴。”
“他多大年纪?”我好奇地问道。
“我想他应该三十一、二岁,我不能确定。但他在军中可是个硬汉,总想做出点不一样的事情给别人看。”杰德边说着边回到了他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