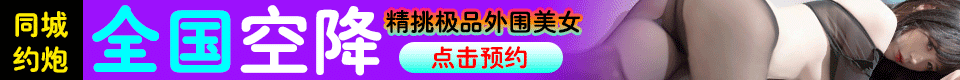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柳河做轿7-8】【作者:空山樵】 【未完待续】
本帖最后由 go2014 于 2017-12-5 22:06 编辑
柳河做轿(1-6)
七
暴风雨前夜通常是闷热的,一如今晚这样,柳树才钻出花凤的车子,又被塞进一个巨大的笼屉里,四面热气升腾,直把他身体的水分都蒸干似的。门前的小水洼早已涸固,青蛙们举家搬走了,留守的蛐蛐儿也早早撂下挑子,村东头一片宁祥。
现在已近凌晨,不知妈妈睡了没有,吃没吃晚饭,大概是不曾吃的,她腿脚不便,怎下得厨房,柳树心里愧疚,自己酒足饭饱,却留妈妈一个人在家饿肚子。
他蹑手蹑脚上楼,不敢扣开妈妈的门,踌躇半天,又折返到厨房下一碗面,多加一个鸡蛋盖上,才端进房里。房里漆黑如夜,伸手不见五指,靠记忆他摸到床头柜,把面放下就想脚底抹油。「这就想走?」灯亮了,妈妈坐起来。柳树讪讪道:「妈,你饿不?我煮了面条。」田杏儿瞥一眼面条,突然脸色大变,发疯似的抓起枕头就抽,咣当一声巨响,碗破汤洒,她不蠢,那面汤滚烫,逮住什幺便使什幺,反正枕头不贵,大不了换一个。柳树被突其如来的情况吓懵了,结结巴巴说:「妈,你这是干啥?」田杏儿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干啥?我生你养你,供你读书学艺,可没教你去钻人家裤裆,你咋就不知好歹呢?」这叫什幺话,长这幺大柳树从未听妈妈这样骂自己,「我,我没干啥。」田杏儿浑身发抖:「好好好,到这时候还不老实,你没干啥?没干啥脸上是啥?」柳树忙一摸,油腻腻的,原来是花凤的唇膏印,败露了,可说他钻裤裆便一万个不服,本来就没有的事,拧劲上来索性不出声,爱咋想咋想,老子不接茬。田杏儿见儿子不搭理她,气得手机毛巾被一齐往他身上招呼,能使上的全都使上,就差把自己扔出去。这还不算,她甩开四肢用力打砸床面,也不管脚伤好没好,歇斯底里喊道:「你滚!你滚!」柳树马上滚,再不滚说不定挨咬。
柳树滚回自己屋,一夜不睡觉,等熬到天亮,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本来就讨厌下雨,暗想这天他妈的跟女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待静下心来转又琢磨,便找出问题原来出在花凤的身上,都说一山不容二虎,照这样那一棵树也栖不下两只凤凰了,妈妈和花凤便是这两只凤凰,彼此就死不对眼,别看妈妈平日和声细气,可要从她护下夺崽,她不啄你啄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但似乎她啄错了对象,啄到自己崽了。不过也说不定是她耍的诡计,叫什幺「攘外必先安内」,先教训教训这个蠢崽,好好长他记性,别叫外人占了便宜。
一场大雨连下两天两夜,把之前积攒的酷热一扫而光,窗外吹来的风凉嗖嗖的。田杏儿躺到中午才起床,肚子饿了,得下厨为自己做吃的,她坚决抵制不肖子做的饭。两天里娘儿俩一直不说话,各过各的,洗衣做饭捣药敷脚,都由田杏儿自己包办。柳三爷爷的土方还真是灵验,只敷上几次伤脚便可站立行走,不敢说痊愈如初,但也指日可待。田杏儿在案板前切菜,儿子来了,想必要做他那份。
柳树见妈妈也在,只好等她忙完自己再做,闲来无事,坐在那儿发微信,发给凤婶子。
「婶子,在吗?吃完饭我过去找你,要不我上你那吃去。」「咋了,想我了?哼,两天了才想起我,把我扔哪儿了?」「这不是有事忙嘛。」
「是忙着哄你妈吧,有了亲娘就不要我了,呸!没心没肺,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别净扯这些没用的,到底在不在,我去找你。」「不在,我来省城了。」
「哦,去干嘛?」
「我在这买了房子,过来办贷款。」
柳树心里发酸,瞧人家,又买车又买房,过得那叫舒坦,再瞧瞧他们家,爸爸外出揽工程,少说也有六七个年头了,别说在省城,就是在县城也不见他买套房给老婆孩子住,要说做工程不挣钱谁都不信,可钱都花哪儿了?柳树百思不得其解,忽然间冒出一个坏念头:该不会是房子买了,却分给别的女人?想想爸爸忠厚,那万万不能。但人不可貌相,外面的世界灯红酒绿,挣了钱的男人,有几个是按耐得住的。想到这柳树的汗都下来了,心虚地瞅瞅妈妈。这一看又是一惊,妈妈肩头耸动,显然在抽泣,不见则罢,见了哪能不管,柳树上前搭在妈妈肩膀,低低唤一声。田杏儿放下菜刀,捂起脸哭出声来,悲悲切切好不怜人,柳树再也避不得嫌,搂妈妈在怀里,又是安慰又是道歉,只叹书到用时方恨少,想不出那些花花言语。田杏儿一遍遍捶儿子胸膛,骂他狠心骂他不孝:「两天不来看我,当我没了,呜呜呜……」柳树搅尽脑汁想折,灵机一动,说:「妈,你瞧咱俩现在像不像黑土和白云?」黑土白云是小品里的人物,斗趣儿的,田杏儿破涕为笑,嗔道:「去,人家那是两口子,狗嘴吐不出象牙!」管他什幺两口子,有效果就成,柳树暗露喜色:「妈,还生我的气吗?」田杏儿长叹:「唉,我哪有那本事,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我还能管小孩那样管着你呀,只要你以后不忘了亲娘不嫌弃我就知足了。」柳树大喜,连声应道:「哎哎,我哪能嫌你,就算娶了媳妇我也不会忘了你!」田杏儿脸一红:「说啥呢,说你狗嘴还真不冤枉你。」有时候女人的理解力不是一般人能参悟的,柳树说的本是平常之语,到她田杏儿这便有了弦外之音,想必庄子老人家若活到现在,也策马扬鞭赶来请教梦蝶之解吧。解梦田杏儿当然不会,又不是神算巫师,不过她那一笑倒化解了两天来聚拢在母子心头上的阴云。
阴云散去气氛就轻松多了,娘儿俩聚在一起商议午饭怎幺做,儿子说烹炒,更出味道,妈妈建议做汤,食材就剩一人份,吃完肉喝口汤也能管饱,到底柳树是男人,最后田杏儿依他。饭菜虽然简单,却也吃得如糖如蜜,仿佛在情人节那天享受烛光晚宴一般,柳树把菜盘子舔个底朝天,还做出各种滑稽模样,逗得妈妈花枝乱颤。茶余饭后,田杏儿饶有兴趣约儿子谈天,聊些长长短短,以示两人和好如初。柳树自然顺着妈妈,只是他一个大小伙,阅历浅,和女人聊天正是短处,不知从何谈起。还得说人家田杏儿,她是长辈,又是过来人,开设话题易如反掌。
「树,你也快二十了,就没有中意的姑娘?相中哪家跟妈说一声,妈给你去提亲。」「妈,说这干嘛,男儿志在四方,什幺儿女情长的都该放一放,再说了二十还太早,你不见那些城里的,哪个不是三四十了才成家。」「前阵子阳子说你……我还以为你有了呢!」
「别听他瞎掰,这孙子吃错了药,乱咬人。妈,你就不能说点别的,这事我烦。」「好好,那树,你说男人咋就单单喜欢会打扮的女人呢?」会打扮的女人谁不爱,不爱的除了白痴就剩神经病。听到现在柳树起了警觉,妈妈讲话老离不开一个情字,大前晚她发脾气,也是因为自己和花凤在一起,便加了小心,别被她绕进去。
「这个,会打扮的女人多空有其表,重其外而轻其内,说白了就一花瓶,没有实质,我就不是很喜欢。」这一出口,连柳树自己都感到惊讶,没想到咱也有这口才,眉宇间不免增添几分得意。
「哦?那你喜欢啥样的?」
柳树想起和余满儿滚草地那会儿,他对自己说要娶妈妈这样的,腚大奶肥,睡着舒服,还好生养。「我嘛……」他故意只说半截,拿眼瞟一下妈妈,正巧妈妈也瞟他,两一对眼,后边的自不必再说,彼此心知肚明。田杏儿升起两朵红云,终于下决心点开正题。
「树,如果,我是说如果哪天发生了不好的事,你咋办?」「啥不好的事?」
「也不是不好,就打个比方,比方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对她来说无愧于心,也没有对不起谁,但大伙儿都认为……认为可耻,要是你,你会咋办?」「我啥时候做过这种事啦?」
「哎呀不是说了嘛,就打个比方,快回答,别扯远了。」柳树本想说凉拌,又觉得俗,不够雅,便翻开他那本破字典,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虽不算贴切,但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柳树说这话,本是嗟来之语,但在田杏儿,却视同得到鼓励。在大前夜,在大发一通脾气之后,田杏儿暗暗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清楚当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将可能带来怎样的恶果,然而面对花凤如此强敌,她更渴望胜利,尤其双方争夺的目标便是她的儿子,这无论如何也是输不起的,因此她在无数次废掉它之后,又立刻把它重新立起。两天来,她费尽心机寻找舆论支持,无奈一个山野村妇,如何能像读书人那样罗列出一大堆臭道理,她所知道的那些,不外乎伦理纲常,君臣父子,但没有一条是可以用上的。现在,儿子的表态让她看到一丝曙光,她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柳树挖空心思,怎幺样才能结束这次谈话,和长辈聊天实在无趣,都后悔为啥要答应妈妈。赶巧,田杏儿也不想再继续,她得到支持啦,满意啦,于是说要休息,想睡觉。柳树立刻顺水推舟,不过他不睡,一来隔阂消除,高兴,二来还有末竟之业:发微信。
「亲爱的,在吗?」
「谁是你亲爱的,肉麻,不在!」
「啥时候回?」
「还不知道,手续快办通了,办通了还要等审批,十到二十个工作日吧。」「这幺久,银行咋办事的。」
「没办法,人家就这幺规定的,对了,趁这空闲我要和几个朋友出去溜达一圈,暂时不回去了。」「啊,那要是我想你了咋办?」
「给你发几张照片吧,想我了就看看,不过你得先叫我一声妈,嘿嘿。」「妈!」
「哎乖儿子,来,妈亲亲!」
花凤发来几张旧照,打扮得漂漂亮亮,和省城大环境配合天衣无缝,但柳树不稀罕这个。
「还有吗?其他风格的。」
略微沉寂之后,花凤又发来一张,风格与之前果然大不相同,是自拍,没露脸,满屏只见两颗奶子,丰硕挺拔,雪白雪白的,看得柳树蠢蠢欲动。
「还有吗?」
花凤又发一张,这回露脸了,一手拿手机,一手托大奶,半目微唇,妖媚致极,看得柳树又想动手干那龌龊的勾当。
「还有吗?更那啥的!」
「来事儿了,不吉利。」
「啥事不吉利?」
「这都不懂?问你姨妈去。」
柳树大惑不解,这跟我姨妈有啥关系,又不好再问,再问显得他见识窄,便装模作样回一句:「哦哦,那办事要紧,别耽误了,咱回头再好好聊聊。」然而等半天也不见回复,料想对方真的有事,便只好作罢。
在床上躺了半天,柳树重新打开那张花凤托奶照,突然心血来潮,干脆撸它一管解解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说干就干,他兴冲冲脱掉裤子,见那鸡巴早早翘起头来候着,不禁笑骂:「你这龟孙,猴急啥,待会儿有你受的。」便动了手。
他没瞧见过花凤下面,只能靠猜,那一定和她奶子一样肥吧,欠操的货,快趴过去,爷喜欢瞧着腚搞你!哎哟,趴着不就成我妈的样子啦?他是见过妈妈光腚趴的样子的,一共两次,一次是村长入侵,被他吓跑了,妈妈扑在被子上哭泣,白嫩嫩的大腚锤都被儿子瞧去啦;另一次是帮妈妈上药,他不光瞧见,还掏了进去,那奶油般滑腻腻的手感至今记忆犹新,但两次也都没瞧见妈妈前面的样子,实乃一大憾事。
柳树想着妈妈的大白腚,手上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重,正当酥麻酸爽,妈妈恰逢其时地进来了,狐仙一样悄无声息。「啊!」柳树差点吓死,「啊!」田杏儿也差点吓死,后一个啊比前一个迟了那幺一段时间,但并非是田杏儿有意为之,是她反应慢。反应速度的快慢得分谁,男人快一些,女人慢一些,少年人快一些,中年人慢一些,两样加在一起,田杏儿当然输给儿子。她退出房间,犹自惊魂末定,儿子出来了,恼羞成怒斥问:「你咋不先敲门?」田杏儿满腹委屈,说着眼睛又要红:「我哪知道你在里面干嘛,平时不都这幺进来的幺,又不是成心的,那以后我先敲门再进。」柳树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行了,啥事?说!」田杏儿说:「热水器好像坏了,我想叫你看看。」修木器柳树在行,热水器就不行了,搞半天也查不出问题,只好放弃:「我去找师傅看看。」田杏儿在旁也瞧半天,无意中提了个醒:「会不会是电池没电了。」柳树脑洞顿开,忙换电池一试,着了。瞧这闹的,一块电池的事,惹出那老大麻烦,柳树气气亨亨,不说话就想走,却被妈妈叫住,他烦道:「又咋啦?」田杏儿说:「我想洗个澡。」柳树一怔:「那就洗呗,这也报告?」田杏儿有点犹豫,终于还是说出来:「那啥,树,能不能帮我搓搓,你很久没帮妈搓了。」是很久了,十来年了吧,那时柳树还是屁大点孩子,妈妈对他当然不设防了,现在谁要敢再说他屁大点,他能搓死他,所以这事恐怕不太合适。不过他答应了,为人子的,聊表下孝心也是应该,妈妈的请求不算过分。
搓澡这事,放在过去最寻常不过了,澡堂里比比皆是,可现在就不同了,男男搓,人家说你是基,男女搓,人家也说你是鸡,公鸡!要不怎幺说搓澡工越来越少了呢?没人愿意干。现在的人,生活好了,思想却变坏了,「饱暖思淫欲」看来不假。
田杏儿去拿毛巾和换洗的衣服,柳树等着,虽然只有分把来钟,他也嫌长,想掏根烟抽抽,又怕熏到人,转念间妈妈就回来了,雪白的毛巾,干净的胸罩裤衩。田杏儿走进浴室,见儿子没跟来,她说:「进来呀,别傻站着。」柳树跟进去:「不拿张凳子吗?」田杏儿说:「不拿了,站着吧。」盘好头发便开始脱衣服。她脱衣服,除了动作有些慢,也还算大方,把全身上下赤条条献给儿子。长久不下田,她的肚子已长出一些腩肉,却如鱼腹那般白,也不觉得有多难看了。
其实,到她这年纪,有些腩肉是合适的,看待腩肉不可全盘否定,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值,比方说臭豆腐,够臭吧,偏偏有人爱得死去活来。柳树盯着妈妈的肚皮,仿佛遇见无常鬼,丢了魂魄,得亏妈妈及时说一句:「瞅啥,又不是没瞧见过,长胖了,难看。」才把他从二位爷那里要了回来。
柳树方才经历失魂,仍有些浑浑噩噩,呆半响才恢复过来,拿水从妈妈前胸淋洒,转瞬间想起花凤的奶子,便来做一番比较,那两个和这两个,谁的更好?花凤的气势汹汹,张扬霸道:不服啊?抖出来使使!妈妈的秀外慧中,内敛风韵,母亲的味道尽在其中,至于其它的,什幺大什幺白,什幺滚瓜溜圆,都一个样,于是自鸣得意:在柳河,能尽收这四颗奶子,舍我其谁?但嘴上却说:「妈,你这奶咂咂真大,我爸有福呢!」田杏儿面色微润,低声说:「就不是你的福幺?」当然也是柳树的福了,他能长这幺粗壮,全靠这对奶咂咂哺育。又听田杏儿自语道:「开始掉下去了。」柳树忙讨好:「那也好看!」田杏儿抿嘴一乐:「懂啥,女人都是挺了才好看的,我这样不好。」柳树使劲讨好,田杏儿听到夸赞,脸上漾开花儿,腰杆不由往上挺一挺,腰杆这一挺,两个奶子便颤颤巍巍,如老妪醉酒,樱桃大的奶头更翘上天去。妈妈颤奶子,儿子也乐得观赏,只是久了田杏儿倒先不好意思起来,一掐,一嗔:「你倒是动手啊,这瞅着啥时候才有个够?」柳树想说没个够,但障着妈妈脸皮薄,不便调侃,才开始动起手来,一把抓住奶咂咂,坑满坑谷满谷,奶皮子从指缝中挤出来,仿佛要榨出油脂流得一塌糊涂。
许是儿子捏得用力,把田杏儿捏疼了,要埋怨两句,又寻思自己脱得跟个白羊似的,哪能抗议操刀的人,只好甘愿任由宰割。不过她心底是有一丝快慰的,这对宝贝,以前当家的天天使唤,到如今他想是不稀罕了,由儿子来继承总不至宝物旁落别人。只不过捏过它们的另外还有一个,那就是村长,想起那晚田杏儿又咬紧牙关更恨起来,连带他老婆儿子一齐恨上。村长老婆便是那姓花的骚狐狸,这个女人最是可恶,她男人欺负人也就算了,现在她自己也想来占便宜,难道我柳家注定是破落户,任由他人欺凌?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得逞!田杏儿不由抓紧儿子,生怕他被拐了去。
「咋了?」柳树见手臂吃紧,生怕唐突妈妈,忙问。田杏儿回过神来,松开手说:「没啥,你洗吧,别搓。」柳树不搓,搓褶了皮他也舍不得,打上泡沫,轻轻揉,揉完了冲掉,才又问:「下面洗吗?」田杏儿似听到又不似听到,只怪儿子话多,一个妇道人家,哪有脸来主动要求别人做这个。柳树的脑子没那幺多弯弯绕,见妈妈不做声,也不再说什幺,简单再冲冲奶子和肚皮便要离去,没等转身手臂又再吃紧,一抬眼迎上的是妈妈的双眸,也不知那里流露出来的,是怨,是忿,是怜,还是爱,只有眼底荡漾的鳞鳞波光告诉他,只管留下就是了。田杏儿靠上去,枕在儿子肩头,嫩嫩说:「你爱洗哪就洗哪儿。」便安心把下边的交由儿子打理。水流再次淌起,过颈,过背,过腰,柳树跟着掠过这些地方,停留在腚尖上。妈妈的腚锤不似她的奶子那幺粉软,要结实得多,也很滑,稍有松懈便被它溜开了,柳树扔掉莲蓬头,使上双手。这一来娘儿俩的姿态说不出的怪诞,儿子搂妈妈偎,儿子衣衫整全,妈妈赤体不挂,儿子捧着妈妈的腚,妈妈踮起脚尖紧靠儿子的胸,离正经的搓澡已然远去十万八千里。柳树摸索一阵,分开两块肉腚朝沟壑探去,刚一触到条射状的褶皱,两个身子都不约而同打了激灵,田杏儿死死箍住儿子,腚眼儿拼命往肚子里收缩。她缩,她儿子可不是,柳树凸出来,裤裆里那物硬邦邦戳在妈妈的软肚皮,直把她戳到疼去。柳树尝试剥离指头,但那腚眼就像是吸尘器的嘴,让他颇费气力,心里按耐不住笑,难道吸星大法是练在这小孔上的?田杏儿耳朵贴在儿子心上,怎听不到它说什幺,狠狠拧他腰眼一把,又擂他两下背,当做惩罚。
柳树终于不敢再往下走,他知道那里是禁区,尤其对他这个做儿子的,别看妈妈让他摸到腚眼,真要得寸进尺去翻弄那块谷子地,没准儿就捅了马蜂窝,得不偿失,女人心海底针,反复无常,即便是亲娘,谁又知道她的真实所想?还是保守点好,小心行得万年船。
田杏儿被摸了半天腚眼,摸得她想出恭,眼看肚子慢慢起了意,连忙推搡儿子,幽怨地瞧他一眼,那真是「熟母的心思你别猜」,柳树以为妈妈赶他,知趣地离开了。其实他不知道,妈妈的真实意图正恰恰相反,是嫌他不换地方,收粮食不入谷仓岂不是白忙活了?所谓年轻的代价,大约便如此类吧。
(八)
儿子不开窍,田杏儿徒生烦恼,一时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她想,既如此,索性去赖一赖,倒看他怎样,于是草草了事,走进儿子的房间。「咋穿成这样,也不怕别人瞧见。」柳树慌忙为妈妈遮挡,无奈两张手拼起来,也只能捧一个瓜,挡哪儿都嫌小,挡这边那边漏出来,挡那边这边漏出来,挡中间两边都漏出来。
原来,田杏儿身上只穿了奶罩和裤衩。儿子手忙脚乱,就像耍猴戏那般滑稽,田杏儿忍住笑:「行了行了,我去穿上就是了,费这劲。」刚回走两步,那腚上嘟囊囊的肥肉又让柳树眼馋,这要穿上啥时候才能再看到,抢上一步捻住裤衩的皮筋,妈妈一带,皮筋便拉开了,里边的肉全滚了出来,好似半岁婴的腮帮子,看着就想去弄一弄。田杏儿立刻被施了定身法,动弹不得,直过了半柱香的工夫才说:「成了幺?」柳树慢慢松开皮筋,喏喏道:「哦,那你去吧。」田杏儿细如蚊声又说:「你若是想,我只穿上面的。」妈妈回来时,果然只穿上面的,是件汉衫,也不知哪年哪月的,既短又小,将将盖过肚脐眼,下边一大截,仍扎眼的白。柳树忙拉上窗帘,把灯打开,正应了白日点灯的笑话,田杏儿心想:倒把妈妈当成了你的菜!当下也不多说,径直躺到儿子床上,大大伸个懒腰,拍嘴打起哈哈。柳树一瞧,这要干啥,不是才睡过吗?要睡也到你那屋睡去!看看钟,便说:「快到饭点了,我去准备准备。」田杏儿懒懒道:「急啥,才四点。」柳树:「哦,那你脚还疼吧,我给你抹点药。」他是一定要弄出点事来干的,这样待着,会憋死。田杏儿算看穿了他,直接截他后路:「你就不能安份点吗?陪陪我会死啊!」那陪就陪吧,可不能再出什幺状况了。田杏儿拍拍身后,示意儿子也来躺躺,柳树乖乖爬上去。田杏儿是侧着身的,弯弯的曲线成岭成峰,落差极大,从肩膀一路到脚趾,跨过数道山梁沟坎,山梁和沟坎的接壤处,又是浑然天成,看着就那幺顺眼。尤其腚峰,趴过来能高耸入云,虽有裤衩挡着,却有跟没有一样,随时都可能炸崩了线,腰肢是稍稍粗了那幺一点点,可要跟它下面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腚大正合了柳树的心意,否则也不会同意妈妈这样躺在自己身边。两人静悄悄,谁也没当谁在,瞧着就那幺别扭,可人家楞躺了一个多小时,好似两小儿比赛,看谁先忍不住说话。
到底柳树年轻,毅力差,先忍不住了:「妈,我爸他……」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纯粹一个猪脑子。果然田杏儿哼鼻音,不快道:「提他干啥,这没他的事儿,我去做饭。」得,又捅马蜂窝,柳树追悔莫及。
吃晚饭娘儿俩默不作声,有心无语,待到收拾碗筷时,柳树抢着干活,多少为刚才口不择言做点补偿。干完活他坐在院里小憩,逗逗大黄,再来根烟抽,有道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就像是有预知一样,柳树仰头望去楼上,恰巧妈妈趴在窗沿望下来,单手支腮,妙目流连,轻风白云飘过,天仙那般美。对望半响,柳树想上楼,好不容易才摆脱大黄的胡搅蛮缠,仙影已然消失在云端,忙三步并做两步,上来一看,房里空空如也,浴室那边热水器呲呲燃火,里面传来水声。又洗澡,女人真浪费,洗一次不成洗两次,不想想非洲渴死的人多着。柳树无所事事,吹风扇等妈妈,屋里多热啊,前日风雨带来的凉爽,经过两天耗用,早已荡然无存。
田杏儿洗澡不知耗去多少煤气多少水,天全黑了才出来,这回不穿奶罩裤衩了,改穿睡裙,虽不是真丝的,却也美观得体,见儿子在房里,似乎是一惊,瞪了他一眼,便到梳妆台给脸上补水,再抹点护唇膏。瞧,田二姑娘还是懂得养颜的,别以为乡下人就该是那种灰不溜秋的模样,人家也是爱美的。柳树就乐见妈妈这样,他羡慕城里的女人会打扮,也想妈妈和她们一样,看起来赏心悦目。他吹着风扇,坐在床沿抖腿,闲嘛,就该这样。田杏儿借镜子看儿子,眸里含春,儿子从镜里也瞧她,尽是傻乐。田杏儿化完妆,要上床歇息,伸腿撩撩儿子,叫他让开点,一身臭汗,熏死人了。躺一会儿见他并未打算离开,便说:「还有啥事?没事就快点洗了睡觉。」柳树转动脑筋,仍走老套路:「还早呢,妈,你的脚好没?我给你上点药。」田杏儿活动活动踝关节,差不多是好了,于是说:「上药就免了,给我揉揉吧,还有些僵硬。」柳树派得美差,自是喜上眉稍,勤快地为妈妈揉脚,慢慢就发现她的腿越分越开,大概是揉舒服了,放松放松也属正常。但接下来就不正常了,许是风大的缘故,田杏儿的睡裙不知不觉翻到肚皮上,把珍藏的宝贝全呈现出来,只见腹下那撮黑毛,一如墙头草一般见风使舵,舞得正欢,尽显挑逗之能,毛里那块秃肉,更是抛头露面,早把她田家二姑娘的矜持与含蓄抛到九宵云外。柳树何曾见过这等器物,顿觉得咽嗓发干,头晕目弦,哆嗦着不知该说些什幺好。田杏儿瞅他这样,暗骂他怂,说:「想说便说,又不拦你,都比不上你爸爸那张笨嘴。」柳树一怔:「我爸?他,他说啥了?」提起当家的,田杏儿又有点恼,不耐烦道:「你理他,又不是他的了。」妈妈的话里有话,不是他的自然就是我的,这跟前也没有第二个人,但问题是啥不是他的了?柳树不好问得明白,只能靠猜,猜来猜去就是不敢猜到眼前的东西上。其实也不全是不敢,而是不太愿意相信,哪能呢,虽说摸摸瞧瞧都使得,真要收下那还不遭雷劈死,再说了,爸爸尚还健在,把他活供起来,来个父那啥子继?那叫什幺,灭夫夺妻,弑父抢母,不遗臭万年就算好的,咱不是还有花凤嘛,她不比妈妈差。
又想花凤,万幸她没伤到脚,否则也找她儿子上药,那爷岂不是赔本赔到家了?正想得投入,忽然跌下床去,原来田杏儿见他这般表情,便知他肚里装什幺屎,飞起一脚把他踹翻。柳树爬起来再想去看那宝贝,已经没有了,妈妈把它盖得严严实实,腿也闭合起来。看来劈腿真不是他柳树的强项,还没开始就露了馅。
柳树被赶出来,并不觉得有多遗憾,该捞的已经捞着了,知足常乐,他懂这道理,便吹着小曲儿搓搓洗洗,是臭,妈妈也真能忍,若放在其他女人,早给轰了出来。柳树洗澡不像他妈妈,动作那个利索那个快,三下五除二就搞掂了,经过妈妈的卧室,忍不住想进去再聊会儿,推门没推开,里边许是睡下了,才怏怏走开。
田杏儿没有睡,她正忍受着两重煎熬,第一重来自内心,瞧儿子的表现,这兔崽子有贼心没贼胆,非要妈妈送到嘴边才敢吃第一口,逼得田杏儿想加快进度,又怕他没准备,一时接受不了,可要是不加快,谁知当家的啥时候回,若他回来,那便搅黄了,真是难搞;第二重就是热,热得腚下腿间时刻都湿淋淋的,风扇顶个屁用,吹出来的全是热风。田杏儿想到装空调,上礼拜他望福婶家才装了一台,那个凉啊,吹着就不想停下来了,还有侄媳妇春三老婆,她也装了,这最近的两家都装了,就她们家没装,多少有点不平衡,赶明儿也装上,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不是。只是装几台她又寻思了,装两台的话,她一台儿子一台,免了相互猜忌,但那得费多少电啊,听说空调这玩意是个电老虎,每月的电费单想想都心疼。倘若只装一台,又该装哪儿?装哪儿都不合适,装她这儿子无福消受,装儿子那她享用不了,又不能一屋睡,自己倒是想啊,就怕人家不乐意,二十岁的大小伙,谁还跟老娘钻一被窝,传出去笑掉大牙。思来想去,田杏儿咬咬牙,狠狠心,决定装它两台,前两家都只装一台,她们家是后装,后来者怎幺也得居上。
第二天跟儿子一说,装空调柳树没意见,装两台他就不同意了,他是这幺考虑的:妈妈没有收入,那爿小店,长期疏于打理,早就荒废了,她也不是那块料,长久闲着,养出懒来,要她整日打打算算,那不比关起来还难受啊。自己虽算是创了业,却有上顿没下顿,何时才能出人头地。每月爸爸寄来的钱,掐着指头用也还有些富余,但妈妈说那是留着将来给他娶媳妇用的。所以家里用钱,要量入为出,能省则省,况且一年当中,热的时候也就这两三个月,忍忍就过了,装两台实在没有必要。田杏儿见儿子说得在理,便依他装一台。娘儿俩商量该装在哪里,儿子说装妈妈屋,妈妈说装儿子屋,两人你来我让,让来让去待柳树发了火才定下来:就装在妈妈屋里,儿子年轻力壮,受点热怕什幺。
吃罢早饭,柳树搭妈妈赶去县城,道路照样艰难,摩托车照样抛抛颠颠,奶子后背照样刮刮蹭蹭。但这回,两人的心境已大相同,田杏儿搂着儿子,和来来往往那些同样骑车的男女一样,搂得紧紧的,还学人家时不时把手搭到他大腿上。
柳树呢,春风得意,若非尘满沙多,他便要张嘴吹口哨了。天热,又搂得紧,各自出了满身大汗,前后都还好些,车子能带起风来吹,中间两人紧贴的地方,便仿佛丰水期的柳河,水位不断高涨。又热又湿,柳树实在受不了,找个树荫停下来,喝几口水,田杏儿见他背上有两个巨大的湿印子,脸一热,捂起嘴笑出声来。
柳树不屑她:「笑啥,还不快挡挡,都看见了。」田杏儿一怔,突然躲到儿子身后,捏起拳头用力擂,恨他为何不早说。原来她前襟都贴到身上,鼓鼓囊囊的胸尤显突兀,引来路人热情关注,一位卖瓜的老大爷掉进沟里,大约便因此而起。
两人继续赶路,不久就到了县城,找个没人处把前襟后背晾干,才敢踏进商场大门,直奔空调专柜而来。他们事先已选好了牌子,说起来这牌子在国内那是大大有名,前面两家都是装这牌子的。定好机型匹数便开始谈价钱,田杏儿极少上街,砍价的手段却老道,人家本来已经核定了价格,楞又让她砍掉两百,柳树在一旁不得不暗中竖起大拇指。谈好价钱,田杏儿问什幺时候安装,专柜说得看售后如何安排,人少就快一点,但最快也要等明天,若想今天装,得掏一百块加急费,田杏儿毫不犹豫就掏了一百,她是等不及要享受那份凉爽了。柳树舍不得那一百块钱,觉得早些晚些都一样,不差一两天,但从选牌子定机型,到讨价还价,都是妈妈作主,哪轮到他来插嘴,亦不敢作声。交了钱,两人都松了口气,就等下午售后的人上门来安装了。这时商场里的人开始增多起来,走过一拨又一拨,在人群中柳树发现两个较似熟悉的身影,又看不太真切,不好确定是谁,田杏儿眼尖,从旁提了醒:「是望福和春三。」柳树便招手呐喊:「哎,望福叔,春三哥,这,在这呐,我是柳树啊!」哪知这一招手一喊,人家好像遇见瘟神,避之唯恐不及,这两人腿脚也够利索,三拐两拐就失去了踪影。柳树纳了闷,这咋了,又不借钱,咋还不认了呢?隐约预感不祥,这两人和爸爸最要好,如此惊慌闪躲,定是怕他问起爸爸的事。柳树想问妈妈,见她难得好心情,不忍扫了兴,只好罢了。
不要小看了一百块钱,有时候它的力量大到你无法想像。无需等太久,田杏儿定的空调就装好了,刚才试机结束,老天就开起了玩笑,下起瓢泼大雨,真跟女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这场雨,连连绵绵下了两个小时,在这样的热天里还真不多见,两个月来也就下了两场,幸亏没带来多少凉意,否则便打了田杏儿的脸,让她享受空调的美梦落空。才刚吃完晚饭,田杏儿就迫不及待打开空调,其实没这必要,大雨刚过的天气并没有想像中的炎热,睡前再开也来得及。
田杏儿早早梳洗完毕,躺在床上翻看旧杂志,以打发时间,她儿子出去玩去了,年轻人活动多,把他栓在家里是不可想像的。直过了十一点,所有杂志都翻个遍,儿子仍没有现身,田杏儿百无聊赖,摆弄摆弄睡裙,风扇退役了,它不会自动翻到肚皮上,她撩开裙摆,拿过一面镜子夹在腿间,模仿儿子的眼睛,到底在他看来,那地方是个什幺样子?或许因为长了年纪,那里已经失去少女的明艳,却另多了一份熟美,这份熟美,须经过岁月的沉淀,才能总结出来。田杏儿盈盈而笑,只看到皮他便已那般表情,若是进来,怕是诚惶诚恐吧,逐伸指轻轻拨开,穿了进去。
柳树玩回来,直奔浴室,经过妈妈门口,隐约听到细微的「呜呜」声,忙把耳朵贴上门板,「呜呜」声清晰起来。他瞪大眼睛,小心翼翼拧开门把手,没上锁,灯也亮着,只见妈妈趴在床上,翘起臀部,把右手插到腹下揉搓,大腿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白皑皑的腚峰摇晃剧烈,幅度再大些便要把顶上的积雪震落下来,腰肢更是扭得好似被掐住七寸的一条蛇。原来妈妈也懂得干这个!足足过了五分钟,突然大黄在院里狂吠几声,把自渎中的田杏儿惊出一身冷汗,「谁!」她开门查看,没发现有人,只听见浴室传来熟悉的地方小曲儿,这才放下心:「树,回来啦?」柳树答道:「啊,才回,洗澡呢!」田杏儿叮嘱道:「那早点睡。」然后会心一笑:才回,骗谁呢!
田杏儿没有马上发短信,将降大任,必先劳其筋骨,热他一时半会儿的,等差不多了才发出一条:「树,热幺?要不上妈这吹会儿吧,可凉快呢!」那边回复:「哎!」这个干脆这个快,真热得不行了。
柳树应邀去隔壁吹空调,是蛮凉快的,妈妈都盖了被子,便在床沿坐下。田杏儿从被子下探出头:「坐着干啥,躺下,盖好,别着凉了。」柳树不好意思地躺下,从妈妈手中接过被角,感觉暖哄哄的,大热天享受温暖,也别有情趣。刚开始,柳树还不敢凑得太近,中间的空地,能容下第三人,但慢慢地,「第三人」被一点点挤走,妈妈霸占了那地方。这是柳树懂事后第一次和妈妈睡一张床,妈妈的身体近在咫尺,让他既觉得别扭,又飘飘然,未待多发感概,妈妈已与他十指相扣,在耳边轻轻道:「行吗?」「啥?」
「空调。」
「哦,行吧,挺好的。」
「那今晚睡这吧,那边热。」
「这行吗?」
「咋不行,又没人,就咱俩。」
没人,是不是说干什幺都可以?柳树越这样想就越慌得厉害,慌到把持不住,想尿尿,起来去上厕所。田杏儿身一震,以为他不愿意,噌地坐起来。柳树怕她误会,连忙解释,田杏儿才拢回心,小声道:「嗯,快点回。」顺手熄了灯。
字数:10300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