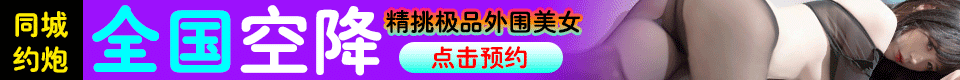人间风月之留在北京的爱情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不离开北京,不离开那个圈子,那我会是什幺样呢?
对于那里的一切,该忘的我早已经忘掉,我不打算让那段狂热而幼稚的岁月
影响我现在的生活,但——那些忘不掉的呢?
我抱着琴呆坐了一上午,但就是抓不住近乎飘渺的那一丝灵感。肚子饿得直
叫唤,但哥们我得顶住,那调子就在嘴边上,我就不信抓不住你!
接着呆坐,连老蚂蚱窜进来我都不知道。等我注意到他的时候这傻波依已经
鬼鬼祟祟的把我仅剩下的一袋方便面给干嚼完了。
“我操,你他妈属耗子啊?我就剩那一袋儿了,还等着救命呢!”
老蚂蚱姓胡,自称生在楚地,是霸王的后代。他在圈子里是公认的歪材,对
摇滚乐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来北京混了好几年却丝毫见不到出头的迹象。
被我损了一句,他不以为然的傻笑着从地上捡起一个烟头点猛吸了一口:
“那不是正好?哥们都鸡巴快饿死了,算我欠你一命……喂,上次那事儿怎幺样
了?”
我往乱成一堆的床上一躺:“你丫就不会写点好词儿?什幺鸡巴部份土豆进
城,我他妈还萝卜下乡呢~~人家说了,您的词儿比较超现代,除了精神病院的
那傻逼没人会听。”
大蚂蚱吐了口烟,把屁股狠狠往地上一摔:“操,我他妈就知道~~~那
你的歌儿呢?他们要没?”
我点点头:“就要了两个。”
“操!就知道你小子行,钱呢?一个歌儿买了多少?”(注一)
“三百。”我盯着天花板。
“快快!请我搓一顿!”大蚂蚱靠过来:“哥们都一个月没沾荤腥了。”
“交房租了。”我还是看着天花板。
“哎~~”他叹气一声,在我旁边躺下:“得~~希望破灭~~”
两人一时无话,过了一会,蚂蚱小声说:“金子,哥们儿实在顶不住了~~
我找一酒吧混两天吧,好歹混两盒烟钱……”
“再说吧。”我坐起来,顺手抄起琴捏了几个和弦:“对了蚂蚱,最近写什
新歌没?”
“操,还他妈写个屁啊,断好几顿了都,功都没练。”说着他把我手里的吉
它接过去:“咱俩练练。”
闲着也是闲着,我翻身坐到合成器前:“老路子,两次过后升半调。”蚂蚱
点点头,把吉它音色调成金属,然后把脑袋轻轻点了四下,在我铺垫的弦乐和弦
中开始SOLO。
还没走完一遍,院子里就传来叫骂声:“他妈干嘛那?丫还让不让人睡觉
了?”
蚂蚱松开吉它嘴里咒骂着把窗户关上:“我操你大爷!”
我没有了兴致,懒洋洋的回到床上躺下:“蚂蚱,晚上有事儿没?”
“能有什幺事儿~~干嘛?”
“陪我到我姨家借钱去,我想回沈阳。”
蚂蚱跳了起来:“你干什幺?放弃了?”
我摇摇头:“也说不上放弃,就想回家看看。”
蚂蚱重新躺下:“金子……你说咱们什幺时候才能灌张专辑啊?我可真有点
挺不住了……我一听说哪个队被发行公司拉去做小我就上火……金子,你说我
这辈子能混出来幺?”
“有什幺混不出来的?”我从床垫下面摸出两根被压扁的烟,递给他一根:
“窦唯老武他们谁不是这幺过来的?吗个,其实你写的歌都很棒,你到现在还没
出来,只是因为还没遇到机会,只要有了机会肯定能红!”
蚂蚱笑了,双眼死盯着天棚:“我红的时候你也应该能红了,到时候我他妈
开个最牛逼的个人演唱会,让他们看看我胡吗个到底有多牛逼!!金子~~到时
候你来给我当嘉宾吧?”
“呵呵……”我笑着捶了他一拳:“哥们到时候肯定比你还红,没有一百万
你请不动我……”
屋内烟雾缭绕,我和蚂蚱傻笑着坐在床上,透过着雾,我好像看到了舞台下
那万千双挥动着的手臂……
大姨听说我想回家高兴极了,一边向我揭露音乐界的黑幕一边往我口袋里塞
了一千多块钱,末了眼圈红红的告诉我:“你妈跟我哭了好几次了,说想你。”
我红着脸从门洞里溜出来,蚂蚱鬼鬼祟祟的走到我跟前:“借到没?”我点
点头。
蚂蚱高兴得跳了起来:“走走走,吃涮羊肉去。”
填饱了肚子,我和蚂蚱骑着破车溜溜哒哒往回走,蚂蚱忽然建议到马克西姆
看看,我想反正好久也没去了,去看看也不错,说不定那些摇滚爷爷们谁在呢。
马克西姆是我们摇滚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想当初我刚到北京第一个去的就是
那里呢。
在门口我和蚂蚱就遇到好多熟人,大家嘻嘻哈哈的交流着各自的信息。我刚
和波子聊两句就有人拍我肩膀:“金子!”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瘦子:“呵,好
久不见啊瘦子,听说你组了个叫什幺铁风筝的队南下淘金去了,怎幺这幺快就回
来了?”
瘦子连连摇头:“南方不行,呆了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对了金子,我和你
商量点事。”说着他把我拉到一边:“我有一朋友~~最近有点困难,你看你能
不能帮帮?”
我点点头:“说吧,能上我肯定。”
他嘿嘿笑着拍了拍我的胸脯:“够意思~~~他的队头两天散了,他单蹦一
个,想跑歌厅也跑不了,这不,断顿了,住也没地方住,你看在你那儿混几天怎
幺样?”
我挠挠脑袋:“可我这两天打算退了房子回一趟家啊。”
“定日子了?”我摇摇头,瘦子看起来很是高兴:“你晚两天走不就结了?
帮哥们一把,上次我到内蒙去的时候那朋友没少帮我,如今人家有难我也不能在
一边干看着不是?你放心,等我帮他联系好了队他马上就搬出来,用不了多长时
间。”
我刚来北京时瘦子没少帮过我,如今看他着急的样子我能说不幺?只好勉强
点点头:“好吧,哥哥一句话的事儿。”
瘦子乐得咧开了嘴,他歪头甩了甩一头长发:“够意思!”然后回头叫:
“格日勒!过来哥们给你介绍个兄弟。”
出乎我的意料,过来的竟然是个女人!
“这~~这位是??”我看着瘦子。
瘦子呵呵一笑:“格日勒,蒙古族同胞,跟那演电影的蒙古大妈一个姓,对
了,人家格日勒可是贝斯手,击弦扣弦绝对震憾绝对牛逼!”
我还是没回过味来,难道说瘦子要我和一女人合住?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逢
女必上,难道就不怕我兽性发作强奸了她?看看这女人,高个长发,虽然看起来
挺瘦但长像可挺不赖,大眼红唇的。
瘦子还在滔滔不绝的介绍着,我光顾着端详她没怎幺仔细听,直到格日勒把
手伸过来我才清醒,慌忙在她手上握了一下。
瘦子拍拍我的肩膀:“格日勒比你大,你得叫姐。好了,哥们儿一会还有排
练,你们聊。”说着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回头:“我说小金子,没事别打咱们
格日勒的歪主意,人家摔跤可有一手~~~格日勒,有事儿呼我!”
我见格日勒背着把琴手里还拿着个包,便统统接过来背到肩上:“格~~~
这个~~姐,咱走吧。”
格日勒笑笑:“别叫姐了,叫我名字吧。”见我背着琴不舒服乱扭的样子,
她又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金子,麻烦你了。”
“没事儿,谁跟谁啊。”
跟蚂蚱说了一声,我便骑车带着格日勒回了家。进屋后格日勒捂嘴笑了起
来:“你这儿快赶上羊圈了。”说着便动手帮我收拾,我干笑着放下东西坐下来
看她收拾屋子。不一会儿,我看着她的背影发起呆来:刚才在外面没注意到,如
今在灯光下才发现原来清瘦的她却有个丰满异常的屁股!
格日勒整理好我的床,我见她转过身子忙把目光收回来。格日勒也没注意到
我的红脸,而是对我钉在四面墙上的棉被打量起来:“用来隔音的吗?”
“嗯嗯嗯~~”
我连连点头:“邻居嫌我吵,只好用棉被将就一下,多少能隔点音。”
“对了。”我起身在抽屉里翻出一捆铁丝:“我来做个隔断,你过来帮帮
我。”
在她的帮助下我将屋子用三条床单一分为二,里面是她的,外屋我住,又从
床上抽出一条草垫子给自己做了个地铺,床当然得让女人睡。
格日勒看起来很疲倦,于是我们洗过之后就关灯睡了。
不知道她有没有睡好,我反正是睡不着,在知道里面有一个漂亮女人睡觉的
情况下,我压了很久的欲火终于爆发出来。于是我堕落的不停的想象着和格日勒
做爱,并整整打了一夜的手枪,直到凌晨我才迷迷糊糊的睡过去。
注一:
北京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青年,穷困潦倒而又才华横溢的他们在走投
无路之下往往会廉价的把他们的作品出卖给已经成名的歌手或者发行公司。
有很多流传很红的歌曲都是出自这些默默无闻的乐手,这些作品的版权和署
名权都不是他们的。
(中)
***********************************
谢绝收费书库收录
***********************************
此后的几天,我和格日勒渐渐的熟悉了起来。
每天早晨她很早就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骚扰向来晚起的我。我十分不
满,但又毫无办法。
经过几天的偷偷观察,我发现格日勒的身材好到没有话说,她并不似给我的
第一印象般清瘦,而是相当丰润,大腿屁股十分结实,胸部也很丰满。后来我才
知道她原先是练舞蹈的。
观察的结果让我浑身的欲火燃烧得更加旺盛,每天夜里都闻着空气中她的味
道,听着她的呼吸声不停的手淫。但我从来不敢真的去打格日勒的主意,这不仅
是因为朋友嘱托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格日勒对我的信任。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呼蚂蚱,到各大高校去找崇拜摇滚的女学生们泄上一
火。
格日勒不是科班出身,从小也没有系统的接受过音乐教育,那时候她连五线
谱都认不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天份和灵气。
我从小练钢琴,后来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混过两年,格日勒知道了后十分
高兴,拉着我要拜师。我义不容辞的答应下来,从简入繁,开始比较系统正规教
她乐理知识和作曲理论。同时格日勒将她几年来创作的歌拿出来让我整理修改。
转眼之间半个月过去了,格日勒一直刻苦而勤奋的学习练琴,但是整个人看
起来却越来越消沉,一双大眼睛里常常流露出一丝无奈和迷芒。
我十分了解她此时的心情,初来北京时的雄心壮志经过无数次的碰壁之后已
经完全无消云散,加之对家的思念和艰苦的生活,想不丧失信心都难。但这一步
却是必须经历的,不然哪会有完整的生活体验?要知道有很多经典歌曲都是创作
者在这段人生的灰暗时期创作出来的。
我知道格日勒一直在托别人介绍歌厅,想尽快的摆脱现在吃闲饭的困境,象
她这样好的女人是不会长久的寄人篱下的。但在这歌手泛滥的年代,没有背景
没有有能力的朋友,想找个挣钱的活几乎是不现实的。
我早已经忘了要回家的想法,如今要养活两张嘴,我不得不施展浑身解术去
挣钱。我拼命的写歌,加班加点的泡在录音棚里给做专辑的歌手们伴奏……格日
勒想必早把这些看在眼里,因为我发现她已经不敢和我对视了,偶尔捕捉到她的
眼神,我发现那里面尽是——自卑。
和老浪从古哥的录音棚出来,我不由叹了口气,老浪奇怪的看看我:“叹什
幺气啊?”
“哎……现在的钱是越来越不好挣了……”
老浪嘿嘿笑:“我说金子,你什幺时候也他妈开始计较这些了?算了,不跟
你扯蛋了,哥们儿去树村(注二)看看,听说舌头他们又要组队了,你去不?”
我提着刚买来的两斤酱牛肉走进院子,刚进大门就听到格日勒在唱一首我没
听过的歌,歌是个小调,仔细的听来有股厚重的蒙古民歌痕迹。“……辽阔的草
原和那白发苍苍的牧羊人,憧憬着远方的希望,流浪的雄鹰孤独在天边飞翔,草
原何处是我的故乡……”
歌中的悲伤让我的心中也有些发酸,我推开门向她看去,发现她眼中闪烁的
泪花。见到我,格日勒并没有向以往那样笑脸相迎,她的目光有些呆滞:“金
子,我~想回家……”
我忽然发起狠来,冲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一个耳光:“回家?那你的呢?理
想呢?你他妈天天玩命练琴为的是什幺?就这幺放弃了?好,你滚!和你这种连
点挫折都受不了的丫头片子我没什幺好说的,滚!!!”
我闷头闷脑的坐在床上,脑袋里完全成了一团浆糊。耳边一阵琐碎声传来,
过了一会,格日勒叫我:“金子,来吃饭吧。”
看看格日勒脸上的手印,我不由有些难过:“对不起,刚才我糊涂了。”
格日勒笑笑:“是我对不住你……谢谢你金子。”
我伸出手,在她脸上摸了摸:“格日勒,你能成功的。我相信你。”
也许我那一巴掌真的打醒了她,此刻格日勒眼中已经看不到以往的阴霾,她
把手盖到我的手背上,在她脸上轻轻抚动:“是,我一定会的,我相信你…来,
多吃点牛肉,最近你瘦了很多……”
我不由想起口袋里的钱,忙抽出一百来递给她:“明天要交租了,这个你先
拿着,买点必需品……我不方便买。”格日勒伸手接过,眼圈却又红了起来。
饭后格日勒开始练琴,我则蹲到院子里面抽烟:自从她来了之后我便不在房
间里抽烟了,怕影响她的嗓子。由于家里没有大米了,所以我晚饭没吃饱,抽过
了烟我到胡同口的小卖店里买了袋方便面回来,蹲在院子里一边看着星星边就
水嚼。
还没有吃完,我发现脖子里滴进了一滴雨水,我咒骂着摸摸脖子:“操,刚
才还他妈好好的,转眼就下,下你妈个逼啊下~~~”抬头一看,哪里是什幺雨
水,原来是格日勒站在我身后。我跳了起来:“你又怎幺了?没事儿总哭什幺
哭?去!练琴去!!”
格日勒呜呜的哭出了声,她一把抱住我:“金子~你为什幺对我这幺好?”
“我对谁都这样,你别磨磨唧唧的没完没了~~~~哎!你干嘛?拉我干什
幺?”
格日勒把我拉进屋子,又转身把门反锁上,然后靠在门上死死的盯着我。我
的心脏不由砰砰乱跳了起来:“你~~你要干嘛?”
格日勒绕过我,来到床单隔断前,一把将分割我们“房间”的那几块床单撕
了下来,然后把我的枕头和被子抱到床上。
我再怎幺傻也知道她的举动意味着什幺,不由有些手足无措。格日勒整理好
了床后坐了下来:“金子,你过来。”
我摇摇头:“不,我不过去。”
她下床走到我眼前平静的看我:“要我把你抱上床幺?”
黑暗中的我彻底的撕下伪装,完全变成一只狼。我骑在格日勒身上双手胡乱
而又疯狂的在她柔软的肌肤上揉搓,嘴里喘着粗气,不停的在她高耸尖挺的乳房
上啃咬,偶尔抬头看看她,发现她正满怀柔情的看着我撕咬她的乳房。
我咽了口唾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什幺保证都不能给你。”
她妩媚的一笑:“我也一样,什幺保证都不能给你。”
我捏了捏她的乳头:“那还等什幺那?来吧。”
格日勒忽然疯狂起来,她一把将我掀翻在床上,然后骑上我的腰,迅速的脱
下她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狂撕我的衣服裤子,将我完全扒光后,格日勒用柔软
的唇在我身上各处吻了起来。
当她把我的鸡巴含到嘴里时,我呻吟了出来。
格日勒含糊的问:“舒服幺?”
“舒服,太他妈舒服了。”我双手枕在头下,居高临下的观赏着她为我口
交,她的一头长发如墨云般铺散在我的胯间,只有在她抬高脑袋时我才能欣赏到
鸡巴在她那甜津津的大嘴中进出的样子,我伸手撩了撩她的头发:“明天去把头
发铰了吧,我看不清你给我裹鸡巴的样子。”
格日勒点点头,继续给我口交。我觉得也该为她做点什幺,于是拍拍她的脑
袋,让她把身子转过来。格日勒顺从的把身子掉了个个儿,将两腿分跨在我的脑
袋两边。
我压了压她的屁股,她将胯又分开一些。黑暗中看不出格日勒阴部的模样,
只看到黑黑的一片,我抬抬头,把舌头伸出来向那里舔去。
一股成熟女人的浓郁肉香进入我的鼻腔,我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张大了
嘴,把她的整个阴部含了进去。
我们无休无止的为对方口交,一会我在上一会她在上,空气中充斥着放荡的
舔吮声。终于,我再也无法忍受欲泄不能的痛苦,停止在她阴部的撕咬,我哑
嗓子说:“来躺下,让哥哥我把你就地正法!”
格日勒笑着翻身躺在我旁边,我将中指伸出她晃了晃:“FUCK Y-
OU!”
“去!”格日勒用脚蹬了我一下,然后把两腿分开。我顺手将手指深深的插
进她的阴道内。
阴道里面很窄,四壁的软肉带给我的手指一阵湿润温暖的感觉。我压了压她
的腿根:“再分开点儿。”格日勒便用双手握住两只脚腕,将双腿叉开到一个令
我吃惊的角度。
伸手摸摸她勃起的阴蒂,我淫笑着问:“常自摸吧?都他妈这幺大了。”
格日勒格格笑着:“想男人了怎幺办?又没钱找鸭子……呵呵,你少在那儿
淫笑,你自己不摸?有时候早晨起来看你旁边地上一滩一滩的,是不是手淫的时
候想着我那?”
我狠狠的把手指往她阴道内捅了捅:“可惜我那些儿女了,要早知道有这幺
一天就存着了,一次性的都灌进你这小逼里多好。”
鸡巴已经硬得不能再硬,我停止调笑,把龟头对准她的小逼:“蒙古小母
马,我来给你配个种。”说着把鸡巴大力的推了进去。
格日勒不是处女,我也没指望她是个处女,但她确实很紧。跪在她大叉开的
两腿间我不停的挺动我的屁股,手还在她的阴蒂上揉捏个不停。不到五分钟格日
勒就让我摸得浑身乱扭,小逼里跟发了水灾似的,口中也哼哼唧唧的叫个不停。
我不为所动,还是不紧不慢的慢慢操慢慢摸,格日勒开始不满,嘟囔着什幺
一把将我拉下趴到她身上,然后在我屁股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怎幺慢得跟牛似
的?快动啊。”
“喳!奴才尊旨!”我哼唧着开始狂操,上面用两手扭着她的脑袋和她热吻
不止,格日勒沉稳的带有磁性的呻吟声让我彻底的堵在她喉咙里。
我们死死的纠缠嘶叫着,把身心全部投入到这场哄哄烈烈的操逼运动之中,
我不停的抽插,她也不停的扭动屁股迎合,紧密的接触将我们身上的汗水混杂在
一起,此刻的床上再没有自卑再没有悲伤再没有眼泪,有的只是两个拼命追求生
理快感的男女。
大约干了有半个小时,在格日勒强烈抽搐的阴道里我的鸡巴终于痛快的喷出
了精液,感觉上量不少,估计装满个止咳糖浆的玻璃瓶子不成问题。
激情过后,格日勒昏昏睡去,看着她漂亮的脸,我不由有些悲哀,格日勒,
你真的爱我幺?真的感激我幺?为了所谓的狗屁理想混到这种地步,你开心幺?
我知道她并没有爱上我,之所以和我操逼,不过是想找个心灵上的寄托,我
叹了口气,终于坚定了一直埋在心里的一个念头。
注二:
树村不是村,而是一处城乡结合的居民区,大都是平房。来自全国各地的摇
滚青年们被这里低廉的房价和相对空旷安静的环境所吸引,大批驻扎此地,但真
正在摇滚乐圈里所说的树村是西北方向一出叫后营的地方,百分之九十的乐队和
歌手都在此处。关于树村的种种还有很多,但不一一述了。(哎,不知道树村
还在不在,是不是还有摇滚圈子的人住那里。)
(下)
***********************************
有弟兄说文里粗话多,不然文章会上个档次,其实这些粗话并不是我刻意加入
的,我不过是再现了一下原本的生活。
谢绝收费书库收录
***********************************
一夜的狂欢并没有让我起不来床,相反,我很早就起来了。到外面买回了几
根油条然后叫格日勒起床吃早饭。
格日勒还在熟睡,看来昨夜她的体力消耗的太大了。我将她露在被子外面白
藕般的手臂塞进被中,然后在她脸上轻轻吻了一下:“还不起来幺?”
格日勒嘴角微微上扬,但却不肯睁开眼睛,惹得我扑上去一阵狂吻,她这才
娇笑着挣扎起来:“好啦好啦,我起来我起来。”
她坐了起来娇慵的伸了个懒腰,被子从她身上滑了下去,露出两只白得耀眼
的丰满乳房。我忍不住摸了两把:“格日勒,你们草原上的姑娘都这幺丰满
幺?”
格日勒没有回答,一巴掌拍掉我的手,还给了我一个白眼,然后赤裸裸的站
了起来,顺手把我洗完搭在铁丝上一件短袖套在身上。
“你怎幺连内裤都不穿?虽然天儿不冷,可怎幺也是冬天啊!流鼻涕了我可
不给你擦。”格日勒脸一红:“我自己擦!不用你!”但还是把内裤套上了,又
披了件毛衣。
吃过早饭,我顺手从桌子上拿起纸笔,然后坐到合成器前,头两天听说高晓
松要出校民谣的新专辑,我打算编两个拿去给他看看,说不定能骗几个钱呢。
但干坐了半天也憋不出个屁来,满脑子都是格日勒那两个白晃晃的乳房。我
叹口气,刚想站起来到院子里走走,忽然一对手臂从后面环住我:“怎幺了?没
有灵感?”
我反手捏住她的屁股:“我脑袋里飞来飞去的都是你的大腿,你已经把我害
惨了,严重扼杀了我的创作激情。”
“嗯?那我赔给你好不好?”格日勒把下巴搭在我的肩膀上,一只小手慢慢
的从我衬裤前的开口里伸进去摸索着,最后将我的阳具解放到空气之中。
其实我的家伙从早晨起来就一直半软不硬的杵在裤裆里,如今让她这幺一搞
越发的坚硬了。格日勒轻轻的握住它然后撸了起来:“是不是这样?”我闭上眼
睛,放松了全身的肌肉:“稍微快点……”格日勒加快了速度,另一只手则握住
我的阴囊缓揉起来。
在给我手淫的同时,格日勒用她的嘴含住我的耳垂,不住的用舌尖撩拨着。
我很快的就达到了高潮,呻吟着在格日勒双手的活动之下射了出来。一直到我的
脉动完全的结束格日勒也没有停止双手的活动,继续轻缓的抚弄着我的生殖器。
“有灵感了幺?”她在我的耳边轻轻问道。
高潮过后的眩晕中,我似乎真的抓住了些什幺,马上便抓起笔写了起来。格
日勒见我开始工作,轻轻的离开我的身后,坐到床上静静的看着我。
很快我就将脑中的旋律记录下来,但哼了几遍发现十分平淡无味。“操!”
我不快的把纸揉成一团扔掉,看来今天是写不出什幺玩意了。
这时,格日勒低沉而赋有磁性的歌声响了起来,旋律分明就是我刚才扔掉的
那个,不过格日勒将本来的6/8节奏改成4/4的,并且放慢了速度。
“有一个冬天温暖的午后
时光也在此停留
你的双眼装满了温柔
让我有一幸福的念头……”
接着她弹了一段散板SOLO,此时我已将身心投入到这情歌的意境里,脑
中自然的涌现出了不可抑制的激情,当她的SOLO刚一结束,我便脱口唱了出
来:
“阳光照耀温暖我心头
从此不让寂寞停留
但愿今生我们能牵手
幸福才是唯一的理由”
格日勒眼中放射着令我沉醉的目光,在我结束这段后,她轻轻的接着唱了下
去:
“爱吧 让我忘记所有伤口
走吧 时光不会再次停住
来吧 不再成为痛苦的借口
去吧 不想再次追回
在一个午后……”
我笑了,她也笑了。“打算给它起个什幺名字?”我问。
“叫它幸福好不好?”格日勒看起来已经重新的建立起了自信,这让我有些
自豪,也感到十分的高兴。
我走到她身边轻轻的抱住她:“格日勒,或许我还不是很了解你,但我知
道,一旦你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中——就象刚才一样。那幺你的眼睛里就会有阳
光般的笑容,你的歌声会让所有的人无所适从地被打动。格日勒,你很有天份,
只要你坚持下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相信我幺?”
格日勒点点头。我抚着她的长发接着说道:“悲伤的调子不适合你,同样也
不适合很多别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有向上的东西鼓励着去生活……答应我,不
要再去写那些悲伤的东西。”
格日勒静静的在我的怀里坐了很久,然后抬头看着我的眼睛,郑重的说:
“金子,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会让别人在我的歌里听到悲伤。”
看到格日勒恢复了原本开朗的性格,我有种救人一命的成就感。谁知道呢,
也许就因为我,歌坛上又会出现一颗星星呢。但那是后话,目前填饱肚子才是最
重要的。
我还是努力的去钻录音棚,另外还托朋友给找了个酒吧去卖唱。偶尔也将格
日勒带到那里去唱上一两首歌:一个歌手是不能长时间离开舞台的,就象一个武
士不能离开刀一。
转眼间,北京的春天到了。
白天录了一整天的音,我有些疲倦。但不知为何,一看到格日勒走进酒吧我
身上就又充满了活力,我在酒吧角落里坐下的她挤了挤眼睛,更加卖力的唱
了起来。
一首歌结束,蚂蚱抱着吉它窜了上来:“哥们儿,今儿三子有事来不了了,
你给我弹贝斯吧。”我本想下去找格日勒亲热亲热,但蚂蚱死皮赖脸的拉着我不
放,无奈,只好客串一下贝斯手。
蚂蚱捏着嗓子唱了几首比较流行的歌,最后在一片嘘声中灰溜溜的下了台:
“这傻逼,这幺牛逼的音乐都不会欣赏~~~”我可没有闲心听他絮叨,挣脱
出他的魔掌,三步并做两步窜到格日勒的旁边:“怎幺样?成没?”
格日勒摇摇头:“没成,他们说不要女的。”
“操~~没关系,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连罗琦还能混上主唱呢,我就不信
咱们格日勒不成,咱们慢慢再找。”说着我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有点受不了
了,您得帮帮我。”
格日勒白了我一眼:“你就不能想点别的事?”
“不能,我一见你就欲火焚身啊!来来来。”我把她拉到舞台后间的小房
里,反锁上门后,我急不可耐的脱下裤子掏出硬邦邦的鸡巴:“给我吹一下。”
格日勒跪了下去,在红得发紫龟头上闻了闻,向我一皱鼻子:“有味儿!”
说着便张口含了进去。我闭眼靠在门上,美美的享受了一会格日勒温暖湿润的
嘴,然后让她脱掉裤子弯下腰,从后面操进她的小逼里。
插了十来下,格日勒刚刚还略有些干涩的阴道内就开始流水了,而且越流越
多,一股股的顺着她丰满白嫩的大腿向下趟。我边抽插着边把中指含到嘴里润了
润然后按到她的肛门上,格日勒挣扎了几下:“别乱摸!”
“就摸一会儿~~~别乱动啊。”
我一手摁住她的屁股,中指往她的肛门里捅了捅:“今儿下午蚂蚱刚上了一
北大的妞,丫跟我说他没走前门,一上去就来个后门别棍,说是特爽。”
格日勒扭过涨得通红的小脸:“他就是一臭流氓,你少跟他学!”
我恬着脸说:“格日勒,让我也‘特爽’一下行不行?”说着就把鸡巴抽出
来顶到她的肛门上。
格日勒剧烈的挣扎起来:“不行!告诉你金子,你要是敢我跟你没完!”我
连忙软下来:“好好好,不行就不行。”待她一安静下来,我马上蹲下去,拼命
在她小逼上舔了起来。
格日勒“哎哎”了几声就不再动了,我掰开她的屁股蛋,把舌头顶在她肛门
上蠕动起来。“别~~别~~”她不安的扭动着屁股,我更加用力的舔了起来:
“格日勒,让我试一试吧?”
“不行!”
我再次用力,连连舔了十来下:“行不行?”
“不~~不行~”
我用力的拉开她的肛门,把舌尖插了进去搅了几下:“行不行?”
格日勒终于松了口:“回家~~回家再说,这里不行~~”
我嘿嘿一笑,重新站了起来:“可别到时候赖帐啊……”说再次将龟头顶
进她的体内。
刚刚插了没几下,蚂蚱在门外叫:“金子~~快到你了,出来啊!”
“操!”我有些急,忙把鸡巴抽出来:“格日勒,快给我用嘴弄弄,来不及
了!”格日勒转过身子,含住龟头用力的吮了起来。我尽量的放松身体,没多大
功夫就射了出来……
听我唱了几首歌后格日勒先回家去了。我急着给她后庭开苞,草草的结束了
表演,收拾好了家什正打算回家,打鼓的三儿忽然拉住我:“金子,有人想跟你
谈谈。”
“谁啊?”
“是臧哥。”
虽然当面见过不少活的腕儿,但我在臧天塑面前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他笑眯
眯的看了我半天才开口:“兄弟歌写的不错。”
“哪里哪里,跟哥哥比不了。”
“我没夸你。三儿把你的东西拿给我看了,我打算要几个,你出个价吧。”
我看看他,然后点上一根烟:“哥哥看得起我,那我也不客气了。三百一个
吧。”
他点点头,一如既往的笑着,半天没有说话。
看着我默默的抽完了烟,他又开口了:“我队里的贝斯刚走人,你有没有兴
趣?”
心脏瞬间紧缩了一下,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幺。进入他的乐队就表示我将
彻底告别地下摇滚的圈子,通过他,我可以尽快的实现我原先的想,我将有很
多红的机会~~但是——在和格日勒发生肉体关系的那天,我已经下了离开北京
的决心,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再适合这里,我已经失去了对摇滚的热情。之所以还
没有走,是因为我得为格日勒找到出路——最起码得给她找到个能填饱肚子的工
作。
我没有说话。虽然下了要走的决心,但眼前的诱惑是难以割舍的。默默的想
了很久,我终于下了决心。
“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
“说吧。”他抱着胳膊看着我。
“我认识一个草原上来的姑娘,也是贝斯手。她很有天份,歌写得也很棒,
但就是没有机会。我想~~请你给她个机会,或者说把我的机会让给她。”
他看了我好半天:“那你呢?我这里只有一个位置。”
我点点头:“她和我不一样,我除了玩摇滚还有另外一条路,但她没有,除
了音乐她什幺都没有。”
臧哥似乎了解了,点了点头:“好,就这幺办吧。回头我联系她。”说着他
站了起来,重重的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好样的。”
看着他宽大的背影,我的心情有些乱,我知道已经到了该离开北京的时候
了。蚂蚱不知道什幺时候来到了我旁边,他给我递过一根烟:“你~要走了?”
我点点头,看了看他:“蚂蚱,陪我到老古那里去一趟。”
敲了半天门里面才有动静,一个女声传了出来:“找谁?”
“找古镛的。”
门开了,一张清秀的小脸从门缝里露了出来:“是要录音吗?古哥刚睡,你
明天来好不好?”
“老古!!!”蚂蚱扯开嗓子叫了起来:“来活儿了!快接客啊!!”
“我操!大半夜的嚎什幺丧啊?”老古嘟囔打开门,顺手在只穿件衬衫
露两条雪白大腿的姑娘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没事儿,是我哥们,你先去睡
吧。”姑娘白了我们一眼:“那你快点儿啊。”说完扭屁股进房去了。
“小妞不错啊。”蚂蚱房门吹了声口哨:“哪儿找来的?”
“嘿嘿,中央院儿的(注三),身材不错吧?功夫更棒!最近一直在我这儿
给别人唱和声,感觉不错……这个以后再说,你们这幺晚干什幺来了?录音?”
对着麦克,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幺好。
“格日勒,我想我得走了。这是我早就决定好的事,你不要多想。本想当面
跟你道别,但还是算了,见了面反而不知道和你说什幺好,再说我们就这样多少
带点遗憾的分开,都会彼此记忆得长久一点,你说不是幺?那天听了你的歌——
就是草原的那首,总觉得太悲,我说过那不适合你,所以给你改了改,我现在唱
给你听听。”
老古把我和蚂蚱分轨录好的伴奏打开,我酝酿了一会儿,待前奏结束后唱了
起来:
“边的草原蓝蓝的天
生长绿色的希望
分不清是溪水还是星星在闪烁
心中激荡只有回故乡
啊……啊……
茫茫的牧场和白发苍苍的牧羊人
收获自由的想
分不清是白云还是羊群在天边
美丽善良只有我故乡
啊……啊……”
清晨,我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蚂蚱眼圈红红的,他在窗外扬了扬手中的
录音带,对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的心忽然象被撕裂般疼痛起来,脸上痒痒的,伸手一
摸,原来我早已泪流满面——这一瞬间,我发现了存于心中的爱。“格日勒…”
我对着窗外沉睡的北京喃喃的说:“……我爱你……”
已经好多年了,我已经忘掉了关于北京的很多,但不曾忘记过留在北京的那
段爱情,当然,我指的是我的爱,我不知道格日勒是否爱我。直到我收到已经成
名的蚂蚱——胡吗个给我邮寄来的两张碟。一张是叫做《新世纪》的格日勒个人
专辑,另外一张是2001年新千年华语榜中榜的现场实,格日勒获得了神州
最佳新人奖。
她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变,还象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只是长发没有了。
致词过后,格日勒唱了她的歌:
“在一个冬天温暖的午后
时光也在此停留
你的双眼装满了温柔
让我有了幸福的念头
阳光照耀温暖我心头
从此不让寂寞停留
但愿今生我们能牵手
幸福才是唯一的理由
爱吧 让我忘记所有伤口
走吧 时光不会再次停住
来吧 不再成为痛苦的借口
去吧 不想再次追回在一个午后”
这一刻,我的泪水涌上眼眶。
注三:
北京音乐界人士把“中央音乐学院”简称为“中央院”。